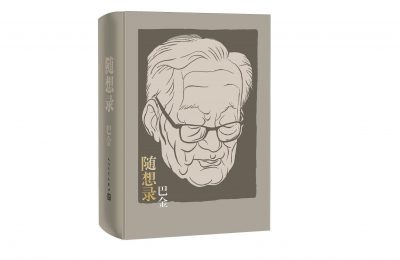巴金编著的《随想录》包括《随想录》《病中集》《真话集》《探索集》《无题集》五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二十年前
天热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藤椅上苦思。脑子不肯休息,我却奈何不得。
“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记不了,不能不让它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因此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时候我回忆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温旧梦,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钟。旧梦也罢,警钟也罢,总有一点隔岸观火的感觉。不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夺去我做人的权利。
我不是在讲梦话,一九六六年我的确做过这样的事情。迷魂汤在我身上起过十年的作用。在一九八三年它还想再一次把我引入梦境,但是用惯了的魔法已经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说:“我要睁大两只眼睛,看你怎样卷土重来。”结果过去的还不是终于过去!我才懂得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不会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事情就是这样:十岁以前我相信鬼,听见人讲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后要经过十座阎王殿,受拷问,受苦刑,我吓得不得了。不但自己害怕,别人还拿各种传说和各样图画来吓唬我。那些时候我整天战战兢兢,抬不起头,的确感到“没劲”。后来不知道怎样,我渐渐地看出那些拿鬼故事吓唬我的人自己并不信鬼,我的信仰便逐渐消失,终于完全消失。到十五岁的时候可以说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说也奇怪,从此连鬼影也看不见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旧事,我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要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喝迷魂汤又怎么样?”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在“文革”受害者中间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再回顾我自己的言行。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协会分会召开的批判大会。这年六月初。我因参加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在北京等地待了两个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宾,然后回机关参加“运动”。
我在作协分会一向只是挂名,从不上班办公。这次运动称为“大革命”,来势很猛,看形势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全国作家大半靠边,亚非客人在西湖活动三天,却不见一位当地作家出来接待,几位北京来的熟人在上海机场告别时都暗示不知什么时候再见,连曹禺也是这样。我看见他们上了飞机,忽然感到十分孤独,我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内心空虚得很。
解放后虽然学习不断,运动不断,然而参加“文革”这样的“运动”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回到机关我才知道给编在创作组里学习。机关的“运动”由上面指定的几人小组领导。创作组组长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点名气,以前看见我还客客气气地打招呼,现在见面几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觉到他要同我“划清界限”了,心里更加害怕,可以说是自己已经解除了武装。我们开会的大厅里挂满了大字报,每一张都是杀气腾腾,绝大多数是针对叶以群、孔罗荪两人的,好像全是判决书。也有几张批判我的大字报,讲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措辞很厉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进大厅,就仿佛进了阎王殿一样。
参加学习后我每天都去机关开会,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后来要按时上班,再后便是全天学习,最后就是隔离审查,由人变“牛”。这是我回机关报到时万万想不到的。我七日到组学习,十日下午便在机关参加批判以群的大会,发言人没头没脑地大骂一通,说以群“自绝于人民”,听口气好像以群已经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还瞥见他坐在这个大厅里埋着头记笔记。总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会的几个头头也不向群众作任何解释,反正大家都顺从地举手表示拥护,而且做得慷慨激昂。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大会连小会开了将近三个半小时,会后出来,一个熟人小声对我说:“不要把以群的消息讲出去。”我打了一个冷噤。她是专业作家,又是党员,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实情况。
晚上我睡前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一点半同萧珊雇三轮车去作协。两点在大厅开全体大会批判叶以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四点后休息。分小组开会,对叶以群最后的叛党行为,一致表示极大愤慨。五点半散会。”我动着笔,不加思考,也毫不迟疑,更没有设身处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处境。我感到疲乏,只求平安过关。一个月后一天上午,我刚刚上班就给“造反派”押着从机关回家,看他们“执行革命行动”。他们搜查了几个小时,带走了几口袋的东西,其中就有这几年的日记。日记在机关里放了将近十一年,不知道什么人在上面划了些红杠杠,但它们终于回到我手边来了。都是我亲笔写的字。
为了找寻关于以群死亡的记录,我一页一页地翻看,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上面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全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所以就在这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后,我也跟着人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实可耻!甚至在我甘心彻底否定自己的时候,我也有两三次自问过:我们的文化传统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我们究竟要不要真实?为什么人们不先弄清是非,然后出来表态?不用说我不会得到答复。今天我也常问:为什么那些年冤假错案会那样多?同样也没有人给我回答。但是我的脑子比较清醒了。
“文革”期间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个,据说他是在八月二日上午跳楼自杀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楼的详情。我主持了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宣读了悼词,我只知道他是让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实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应当由什么人负责,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许我永远不会明白了,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别人说了算”,也从不要求知道真实。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后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①却是在他自杀后的一段长时期,知道傅雷的绝笔则是在他辞世后的若干年了。通过十几年后的“傅雷家书墨迹展”,我才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土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词称赞我的一些朋友,它们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们放射出一种独特的光芒。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他们树立了一个批判活命哲学的榜样。我记得在反右时期还写过文章批驳“不可辱论”,我赞同打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写这种文章其实也是为了活命。当时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顾全面子,那么在生死关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天保佑!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亡友们又接连不断地给我敲响了警钟。
以群死了,对罗荪的批判照常进行。机关的革命派动员我写揭发罗荪的材料,创作组的头头也要我写揭发孔和别人的大字报。我不会编造,只能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革命派不满意。压力越来越大,攻击我的大字报渐渐地多了起来。作家中王西彦是最先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后来说:“我一觉醒来,才知道已经给市长点了名成了反革命。”吴强和魏金枝先后被赶出创作组,师陀接着也靠了边。我还在挣扎,有一天上午我去机关,创作组只到了柯灵、白危和我三个,有人告诉我们,别人都有事,要我们到资料室找个地方自学。以后我们三个人,就脱离了创作组在资料室二楼自学。说是自学,也无非写点交待检查。
形势越来越紧,我也看得出来对我的包围圈越来越缩小,但是我还在安慰自己:组织上对待我跟对待师陀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学习的地方在食堂,每天还得做点轻微的劳动。但是过了几天,柯灵就给电影厂揪走了。只有白危和我还在资料室学习。到九月初有人(一位工人作家)来通知我说我态度不老实,革命群众要对我采取行动,于是开始了第一次的抄家。这次抄家从上午抄到下午,连吃中饭的时间在内大约有六七个小时(来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们家吃饭,饭菜由里委会送来)。后来听人说“这次抄家还是保护性的抄家,上面叫多带些封条来”。原来还有所谓“毁灭性的抄家”,就是将你家里的一切坛坛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扫地出门。我们机关害怕外面有人“乘火打劫”,或者搞“毁灭性抄家”,便先动手将我的书橱全部贴上封条,把重要的东西完全带走。临走时,革命派还贴了一张揭发我的罪行的大字报在我家门廊的入口处,一位头头威胁地对我说:“你再不老实交待,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到大门口,看你以后怎样过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门口贴上这样一张大字报,过路人都可以进来为所欲为了。我想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的。我对自己不再存什么希望了。
然而我还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我好象已经落水,还想抓住一块希望的木板游到岸边。其实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罗荪、王西彦、吴强、师陀、魏金枝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批斗了,不但跟他们没有区别,而且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一个时期白天在机关,我一天几次给外地串连的学生叫出去当众自报“罪行”;晚上还要在家应付一批接一批的住在附近的中学生,请求他们不撕掉书橱上贴的封条,拿走书或别的东西。有一个时期我给揪到工厂、农村、学校去游斗,又有一个时期我被带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我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牛棚”里待了若干年,最后让“四人帮”的六个爪牙用他们的名义给我戴上无形的“反革命”帽子。这就是文件上所谓“打翻在地,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现了奇迹,一夜之间以“旗手”为首的帮伙们全给抓起来,关进牢房,我就真会永远见不了天日了。
我不是写小说,也不是写回忆录,并不想在这里多写详情细节。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想起另外两位在“文革”中逝世的好友陈同生和金仲华,我今天还感到痛心。我六六年开过亚非作家会议回到上海还和他们几次交谈,他们给过我安慰和鼓励。在同一个城市,他们的家离我的住处很近,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死亡的日期。金仲华孤寂地吊死在书房里,住在楼下的八旬老母只听见凳子倒下的响声。陈同生据说伏在煤气灶上死去,因此断定他“自尽身亡”。可是他在隔离审查期间怎么能去开煤气灶?而且,他死前不久还写信告诉熟人说明自己绝不自杀。过了十八年,连这件事情也查不清楚,连这个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说是为死者平反昭雪,难道不就是让亡灵含恨九泉?!
万幸我总算熬过来了。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难过,然而在人世间我留恋很多,许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我决定要尽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说是争取彻底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作人”,过去我的说法有些夸张,我从小就不喜欢形式主义,我举手高呼“万万岁!”,也不过是在保护自己。我们口口声声说是为“新社会”,可是这“新社会”越来越不被我们理解,越来越显得可怕,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比我先掉进黑暗的深渊。比我小十三岁的萧珊患癌症得不到及时治疗含着泪跟我分离。
整整过了二十年。我也害怕重提叫人心痛肠断的往事。但是二十年来一直没弄清楚的那些疑问,我总得为它们找到一两个解答。否则要是我在泉下遇见萧珊,我用什么话去安慰她?!
所以我一直在想,不断地想,我仿佛又给扔在油锅里用烈火煎熬。尽管痛苦难熬,但是在我身上不再有迷魂汤的作用了,虽然记忆力衰退,可我的脑子并不糊涂。我还记得二十年前回到机关参加“运动”,当时我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国家有一部一九五四年的宪法,我的公民权利应当受到宪法的保障,这宪法是全体代表投票通过的,其中也有我的一票。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生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连几张大字报也比不上。二十年前我就是这样走进“牛棚”的,宪法已经失踪,人权早被践踏,我高举“红宝书”,朗诵“最高指示”,由人变兽,任人宰割。尽管那些年我受尽侮辱,受够折磨,但我还是不能不责备自己为什么不用脑子思考?!作为知识分子,我的知识表现在什么地方?“四人帮”称我为“反动学术权威”,我唯唯诺诺,早把“学术”抛在脑后了!
过去的事也只好让它过去,有人不想旧事重提,有人不能不旧事重提,我属于后者。因为记住过去的教训,我才不怕再次上当。只有承认每个公民的权利,才能理直气壮地保卫自己。没有人愿意我们国家里再发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让大家都牢牢记住那十年中间出现的大小事情。最好的办法我看只有一个:创办“文革”博物馆。
六月十九日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六年九月四至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① 玉碎:一九七九年,日本作家开高健发表了小说《玉碎》。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