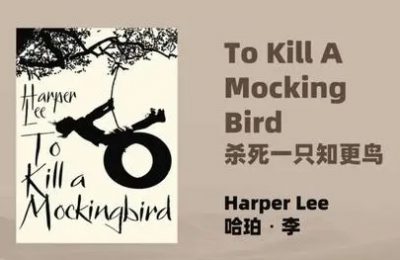《杀死一只知更鸟》是美国女作家哈珀·李发表于1960年的长篇小说。成长总是个让人烦恼的命题。成长有时会很缓慢,如小溪般唱着叮咚的歌曲趟过,有时却如此突如其来,如暴雨般劈头盖脸……三个孩子因为小镇上的几桩冤案经历了猝不及防的成长——痛苦与迷惑,悲伤与愤怒,也有温情与感动。这是爱与真知的成长经典。《杀死一只知更鸟》获1961年普利策奖。美国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书,英国青少年最喜爱的小说之一。美国中学推荐课外读物。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获第25届奥斯卡三项大奖。美国电影协会评选的“100名银幕英雄与恶人”中,派克主演的芬奇律师名列英雄第一位。作为史上最受喜爱的小说之一,《杀死一只知更鸟》已获得显赫声誉。它赢得过普利策奖,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售出超过三千万册,并曾被拍成,备受欢迎的电影。
杰姆十二岁了。他变得很难相处,说话做事颠三倒四,喜怒无常。他胃口惊人,还一再让我别烦他,于是我去请教阿迪克斯: “他是不是肚子里生了蛔虫?”阿迪克斯说不是,杰姆是在长大;我对他要平心静气,尽量少去打扰他。
杰姆像是变了个人,这一切就发生在短短几个星期之间。杜博斯太太才入土几天,尸骨未寒——杰姆当初似乎很感激我陪他一起去给杜博斯太太念书,然而,仿佛在一夜之间,他不知道从哪儿学来了一套莫名其妙的价值观,还试图强加给我,有好几次,他居然教训说我应该如何如何。在一次争吵之后,杰姆冲我吼道: “你也该有个女孩样了!要守规矩!”我大哭起来,跑去找卡波妮。
“别因为杰姆先生的话太生气……”她开口劝道。
“杰姆先生?”
“是啊,他差不多可以叫‘杰姆先生’了。”
“他根本没那么大,”我抗议道,“他就是欠揍,可惜我个子不够大。”
“宝贝儿,”卡波妮说,“杰姆先生在一天天长大,我也没办法。他现在更愿意一个人待着,捣腾男孩子喜欢做的事儿。你要是觉得一个人太孤单,就到厨房来吧。咱们在这儿有好多事儿可做呢。”
那年夏天刚开始还不错:杰姆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在迪尔到来之前有卡波妮做伴,也还好。每当我出现在厨房里,卡波妮似乎都很开心。我在一旁看她做这做那,也开始渐渐认识到,当个女孩子还是需要学会一些技能的。
可等到了暑假,迪尔却没能如约而至。我收到了他寄来的一封信,还有一张照片。他在信中说,他有了个新爸爸,并且附上一张照片给我瞧,还说他今年暑假必须留在默里迪恩,因为他们俩打算造一条渔船。他的新爸爸和阿迪克斯一样是个律师,不过比阿迪克斯要年轻得多,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的面孔。我为迪尔得到这样一个新爸爸感到高兴,但这个消息也让我倍感沮丧。迪尔在信的末尾说他会永远爱我,让我不要担心,还信誓旦旦地保证,等他一攒到足够的钱,就来跟我结婚,所以恳请我多多写信。
虽然我有了迪尔这个长期稳定的未婚夫,但也丝毫不能弥补他来不了的缺憾。我的暑假,就是迪尔在鱼塘边抽他自制的烟卷,眼珠子骨碌碌乱转,琢磨着各种把怪人拉德利引出来的鬼主意;就是迪尔趁杰姆把目光投向别处的时候踮起脚,伸长脖子,飞快地轻吻我一下;就是我们有时候真切体会到对方对自己的渴望和思念——虽然我以前从未意识到,但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有他的日子,生活有条不紊;没他的日子,简直不可忍受。我就这样凄凄惨惨地过了两天。
可是好像这些还不够我受的,州议会又召开紧急会议,阿迪克斯足足有两个星期都不在家。州长急于清理陈规陋习,就像清除附着在船体上的藤壶;伯明翰市一连发生了好几起静坐罢工;城市里领取救济面包的队伍越来越长,乡村里的人也越来越穷困。但是这些与我和杰姆的世界相隔十万八千里远。
一天早晨,我们惊奇地发现,《蒙哥马利新闻报》上居然刊载着一幅漫画,标题是“梅科姆镇的芬奇先生”。漫画里画的是阿迪克斯光着脚,穿着短裤,被人用一条链子拴在桌边,正在一块写字板上奋笔疾书,旁边有几个轻佻的女孩在对他大呼小叫: “哟——嗬!”
“这是一种赞美,”杰姆向我解释道,“他在花费时间做一些如果没人做就搞不定的事情。”
“哦?”
杰姆近来不光脾气见长,还经常摆出一副让人抓狂的自以为是的派头。
“噢,斯库特,比方说,重新制定各县的税收制度什么的。这种事情对大部分人来说非常枯燥无趣。”
“你是怎么知道的?”
“喂,走开,让我一个人待会儿。我在看报纸呢。”
我当即起身去了厨房,杰姆算是称心如意了。
卡波妮正剥着青豆,突然说: “这个星期天,你们俩怎么去教堂?”
“我看没什么啊。阿迪克斯给我们留了要捐献的钱。”
卡波妮眯起了眼睛,我知道她脑子里在想什么。“卡波妮,”我说,“你知道我们会乖乖守规矩的。我们都有好几年没在教堂里惹祸了。”
卡波妮显然还记得那个下雨的星期天,当时我们既没有父亲陪伴,也没有老师管着。主日班的孩子们顿时成了脱缰野马,一伙人竟把尤妮丝· 安· 辛普森绑在一把椅子上,关进锅炉房里。后来,我们把这件事儿忘得一干二净,集体排队上楼去了教堂大厅,安安静静地听牧师讲道。忽然,暖气管发出吓人的“𠳐𠳐𠳐”的声音,这声音响个没完没了,直到有人去寻根究底,把尤妮丝· 安带了上来。尤妮丝· 安说她再也不想扮演沙得拉了——杰姆· 芬奇说,如果她对上帝有足够的信心,就不会被烧死,不过待在锅炉房里实在太热了。
“再说了,卡波妮,这也不是阿迪克斯头一回离开我们。”我争辩道。
“你说的没错,可他每回都要确定你们的主日学校老师会在那儿才行。这次我没听他说过——大概他是忘了。”卡波妮挠了挠头,忽然绽开了笑容,“你和杰姆先生明天跟我一起去教堂怎么样?”
“此话当真?”
“你愿意吗?”卡波妮咧嘴一笑。
卡波妮以前也下狠力气给我洗过澡,不过跟那个星期六晚上监督我沐浴更衣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她让我从头到脚打了两遍香皂,每打完一遍都在澡盆里用清水冲洗干净,还把我的头按在脸盆里,打上“八角牌”香皂和橄榄香皂,使劲儿搓揉了一通。本来她都有好几年对杰姆完全信任,让他自己洗澡了,可是那天晚上,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闯进了杰姆的私密空间,结果惹得杰姆发起火来: “在这个家里洗澡全家人都要来围观吗?”
第二天早晨,她起床比平时早了些,好“把我们的衣服检查一遍”。卡波妮每次在我们家过夜,都睡在厨房里的一张折叠床上。那天早晨,我发现折叠床上摊满了我们的礼拜服。她给我的裙子上了那么多浆,我一坐下来,裙子就鼓得像个小帐篷。她非要我穿上蓬蓬裙,还在我腰间紧紧地扎上了一条粉红色丝带。她用一块冷油饼反反复复擦我的漆皮鞋,直到能照见自己的脸才罢休。
“我们这像是要去参加狂欢节啊,”杰姆说,“卡波妮,干吗要这么折腾呢?”
“我可不想让人乱嚼舌头,说我没把孩子们照顾好。”她嘟嘟囔囔地说,“杰姆先生,你穿那套西装可千万不能配那条领带。它是绿色的。”
“绿色的怎么啦?”
“西装是蓝色的,你没看出来吗?”
“嘻嘻,”我大叫起来,“杰姆是色盲。”
他气得脸通红,卡波妮急忙制止道: “你们俩都别胡闹了。今天我们去首购教堂,你们得面带微笑。”
首购非裔循道宗教堂坐落于镇子以南的一个黑人居住区,在老锯木厂车道的对面。那是一座油漆斑驳的木架建筑,是梅科姆唯一一座有尖塔和吊钟的教堂。这座教堂是获得自由的奴隶们用挣来的第一笔钱买下来的,所以被称为“首购”。黑人们星期天在这里敬拜上帝,有些白人平日里则在此聚众赌博。
教堂的院子地面是硬陶土,旁边的墓地也是一样。如果有人死的时候正赶上旱季,尸体就只能先用冰块盖上,等到雨水让泥土变得松软起来再下葬。墓地里有几座坟墓前竖着残损的墓碑,新一些的坟墓用亮闪闪的彩色玻璃和破碎的可乐瓶圈了起来。还有的坟墓上安插了避雷针,守护着不安宁的灵魂;几个婴儿的坟头上摆放着烧剩下的蜡烛头。这是个乐融融的墓园。
我们走进院子,一股苦甜参半的温暖气息扑面而来,那是从一身洁爽的黑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混合了“爱之心”发乳、阿魏、鼻烟、“霍伊特”古龙香水、布朗骡子牌嚼烟、薄荷和丁香爽身粉的味道。
看到我和杰姆跟着卡波妮走了进来,男人们立刻后退一步,摘下帽子,女人们则双臂交叉,放在腰上,这是他们平日里表示恭敬的姿势。人群向两边分开,给我们让出一条窄窄的过道,一直通到教堂门口。卡波妮走在我和杰姆中间,时不时地回应那些和她打招呼的衣着鲜艳的邻居。
“卡波妮小姐,你在搞什么鬼?”一个声音从我们背后传来。
卡波妮抬起手按住我们的肩膀,我们停下脚步,扭头一看,只见在我们身后的通道上,站着一个高个子的黑女人。这女人单脚点地,斜立在我们面前,左胳膊肘支在后腰上,手掌向上翻起,指向我们。她长着子弹形状的脑袋、奇奇怪怪的杏子眼、笔直的鼻子和印第安弓一般的嘴巴,看上去约摸有七英尺高。
我感觉到卡波妮的手使劲儿抓住了我的肩膀。“卢拉,你想干什么?”她问。我以前从来没听见过她用这种腔调说话。她语气平静,带着一丝轻蔑。
“我想问问,你干吗带白人小孩来黑人教堂?”
“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卡波妮说。她的声音听起来还是那么古怪,跟这儿的其他黑人一个腔调。
“这么说来,你平时在芬奇家也是客人喽。”
人群里响起一阵嘤嘤嗡嗡的私语声。“千万别生气。”卡波妮小声叮嘱我,可我发现她帽子上的玫瑰花在剧烈地颤抖。
这时候,卢拉朝我们一步步逼近,卡波妮叫道: “站住,你这黑鬼!”
卢拉停住了,但嘴上还是不依不饶: “你没有理由把白人小孩带到这儿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教堂,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教堂。卡波妮小姐,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教堂吗?”
卡波妮说: “我们信仰的是同一个上帝,难道不对吗?”
杰姆插了一句: “卡波妮,我们还是回家吧,他们不欢迎我们到这儿来……”
我同意他的话:这些人不欢迎我们。我感觉到,并不是看到,人群正朝我们逼近。他们似乎在慢慢围拢过来,可是当我抬头看卡波妮的时候,发现她眼睛里带着笑意。等我再顺着通道望过去,卢拉已经没影儿了。在她原来站的地方,涌上来黑压压的一群黑人。
一个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那人正是泽布,镇上的垃圾工。“杰姆先生,”他说,“我们非常高兴你们能到这儿来。别理那个卢拉,因为塞克斯牧师警告过她,说要按教规处罚她,所以她才没事儿找事儿。她从老早以前就爱惹是生非,满脑子怪念头,而且蛮横无礼——但我们很欢迎你们来。”
听了这一番话,卡波妮便带着我们朝教堂大门走去,塞克斯牧师在门口问候了我们,然后引领我们走到前排座位。
首购教堂没有天花板,里面也没有刷漆。顺着墙壁摆放的铜支架上挂着一盏盏没点燃的煤油灯;充当座椅的是一排排松木条凳。粗陋的橡木讲道坛后面挂着褪了色的粉红丝绸条幅,上面写着“上帝即爱”——除了一幅影印的亨特作品《世界之光》以外,这是教堂里唯一的装饰。这里也看不到钢琴、管风琴、唱诗本和教会活动手册——要说起来,这些本是教会必备的,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能看到。教堂里光线昏暗,给人一种阴湿的凉意,不过随着聚集而来的人越来越多,这种阴凉的感觉就被驱散了。在每个座位上还有一把廉价的硬纸扇,上面用俗艳的色彩描绘出客西马尼花园,捐赠人是廷德尔五金公司(广告语是:品种齐全,有需必应)。
卡波妮示意我和杰姆坐到前排座位的最里头,她自己插在了我们俩中间。她在手提包里摸索了一番,拽出一块手帕,解开系在一角的零钱,递给我一枚一角钱硬币,又拿出一枚给了杰姆。“我们自己带了。”杰姆小声说。“你们的留着吧,”卡波妮说,“今天你们是我的客人。”杰姆脸上闪过一丝犹豫不决的神色,显然是在是否留下自己的硬币这个道德问题上经历了一场小小的思想斗争,结果还是他天生的谦恭占了上风——他把自己那枚硬币放回了口袋。我照他的样子,也收回了自己的硬币,但没有一丝不安。
“卡波妮,”我轻声问,“唱诗本在哪儿?”
“我们没有。”她回答道。
“那怎么……”
“嘘——”她制止了我。塞克斯牧师正站在讲道坛后面望着台下的众人,等着听众平息下来。他身材粗短结实,黑西装,黑领带,白衬衫,金表链借着从毛玻璃窗透进来的光线,闪闪发亮。
他说: “弟兄姊妹们,今天早上,我们特别高兴地迎来了两位客人——芬奇先生和芬奇小姐。你们都认识他们的父亲。在我开始之前,先给大家念几个通知。”
塞克斯牧师从一沓纸中翻出一页来,拿在手里,然后伸直胳膊,举到一臂开外,念道: “下星期二,传道会在安妮特· 里夫斯姊妹家聚会。带上针线活。”
他接着又念起另外一张: “你们都知道,汤姆· 鲁宾逊弟兄惹上了麻烦。他从小就是我们教会的忠实成员。今天,还有接下来三个星期募集的善款,都将送给他的妻子海伦,帮助她补贴家用。”
我捅了捅杰姆。“这个汤姆就是阿迪克斯替他辩护……”
“嘘——”
我转向卡波妮,可还没等我张嘴说话,她就阻止了我。无奈之下,我只好把注意力集中在塞克斯牧师身上,他好像也在等我归于安静。“下面请乐长引领我们唱第一首赞美诗。”他发了话。
泽布从座位上站起来,顺着中间的通道走到台前,面对着大家。他手里拿着一册破破烂烂的唱诗本,翻开来说: “我们来唱第二百七十三首。”
我再也忍不住了。“没有唱诗本可怎么唱啊?”
卡波妮笑了。“别吵,宝贝儿,”她悄声说,“你马上就知道了。”
泽布清清嗓子,开始朗读歌词,声音就像从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
“河之尽头,有彼乐土。”
真是神乎其神,上百个声音同时响起,抑扬顿挫地唱起了泽布念出的歌词。等最后一个音节以沙哑的哼唱收尾之后,泽布又念出:
“芬芳甜美,永恒之都。”
歌声再一次充盈在我们周围。就在余音缭绕之际,泽布已经接上了下一句: “信念载我,抵达彼岸。”
见大家犹犹豫豫,泽布又一字一句地重复了一遍,大家才开始放声高歌。到了合唱部分,泽布合上了唱诗本,示意大家可以不用借助于他的提示自行唱下去。
当唱到末尾的“狂欢”二字,尾音渐行渐弱的时候,泽布又念出: “遥遥乐土,河水闪烁。”
一句接着一句,大家用简单的和声跟随泽布吟唱赞美诗,直到最后在忧伤深沉的低吟中结束。
我看看杰姆,他正从眼角望着泽布。我也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我们俩都真真切切地听到了。
塞克斯牧师接下去开始呼唤上帝赐福给那些遭受病痛和苦难的人,这个过程和我们教会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他把神的注意力引向了几件具体的事情。
他在布道中对罪恶进行直言不讳的谴责,也对他身后墙上的条幅内容做了严肃的阐释:他告诫信徒们要抵制种种罪恶的诱惑,比如烈酒、赌博和行为不轨的女人。私酒贩子已经给黑人区带来了很多麻烦,但女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套说辞又来了,我在自己教会里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不得不领受“女人不洁”的教义,这似乎在所有牧师的脑子里都是根深蒂固的。
在此之前,一个礼拜日接着一个礼拜日,我和杰姆反反复复听到这样的布道,不过这次有一点不同。塞克斯牧师更加灵活自由地利用他的讲道坛来表达他对某些人自甘堕落的不满:吉姆· 哈迪已经有五个星期没来教堂了,康斯坦斯· 杰克逊最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她总是跟邻居吵嘴,处境很不妙,她是黑人区有史以来第一个为了刁难邻居而竖起尖刺栅栏的人。
塞克斯牧师结束了讲道,站在讲道坛前面的一张桌子旁边,要求大家做晨奉,这个程序在我和杰姆看来也有几分奇怪。信徒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前去,往一个黑瓷咖啡罐里丢进五分或一角硬币。我和杰姆也照做了,在我的一角硬币当啷一声丢进去的时候,我听到轻轻的一声“谢谢,谢谢”。
让我们吃惊的是,塞克斯牧师竟然把咖啡罐里的硬币一股脑儿倒在桌子上,又划拉到手里,一五一十地数了一遍,这才直起身来说: “还不够。我们必须凑够十美元。”
人群骚动起来。“你们都知道这钱是干什么用的——汤姆进了监狱,海伦没法丢下孩子去干活儿。要是每个人再多捐一角钱,就凑够了……”塞克斯牧师朝坐在教堂后排的一个人挥了挥手,喊道: “亚历克,把门全都关上。凑不齐十美元谁也别想出去。”
卡波妮从手提包里扒拉出一个装硬币的破皮夹子。她把一枚新崭崭的两角五分钱硬币递给杰姆,杰姆小声拒绝道: “好了,卡波妮,这回我们可以把自己带来的放进去。斯库特,把你那一角钱给我。”
教堂里变得闷热起来,我突然想到,塞克斯牧师是有意要从这些教徒身上“蒸”出他想要的钱来。纸扇呼啦呼啦摇了起来,人们的脚在地上刺啦刺啦划来划去,平常嚼烟草的人烟瘾犯了,一个个痛苦难耐。
塞克斯牧师突然严厉地大喝一声,把我吓了一跳: “卡洛· 理查德森,我还没见你上来过。”
一个穿卡其布裤子的瘦男人顺着通道走上前去,丢下了一枚硬币。人群里发出一阵低低的赞叹声。
塞克斯牧师又说道: “我希望你们所有没孩子的人做出一点儿牺牲,每人再拿出一角钱,这样就凑够了。”
经过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十美元终于凑齐了。门刚一打开,一股暖风吹进来,顿时让大家恢复了生气。接下来,泽布带领信徒们一句句朗读《在风暴肆虐的约旦河岸》,然后礼拜就结束了。
我想留下来到处看看,卡波妮却硬推着我顺着过道往外走。在教堂门口,她停下来和泽布一家聊天,我和杰姆就和塞克斯牧师说起话来。我有一肚子的问题,都快憋不住了,但还是决定留着去问卡波妮。
“你们今天能来,让我们感到特别高兴,”塞克斯牧师说,“你们的父亲是我们教会最好的朋友。”
我的好奇心终于爆发了: “你们所有人都给汤姆· 鲁宾逊的妻子捐款,这是为什么呢?”
“你没听说是为什么吗?”他反问道,“海伦有三个孩子,她没法出去工作。”
“她干吗不把孩子带上呢,牧师?”我还是不明白。黑人带上孩子在田地里干活是常有的事儿,父母劳作的时候,哪里有阴凉处就把孩子放在哪里——小娃娃们常常坐在两排棉花之间的遮阴处;还不能坐起来的小宝宝用带子绑在母亲的后背上,或者躺在多出来的棉花袋里。
塞克斯牧师迟疑了一下。“实话告诉你吧,琼· 露易丝小姐,海伦这些日子很难找到工作……等到了采摘季节,我想林克· 迪斯先生会雇她去帮工。”
“为什么找不到呢,牧师?”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我就感觉到卡波妮的手按在了我的肩膀上。迫于她的压力,我只好说: “谢谢您让我们到这儿来。”杰姆也道了谢,然后我们就一起往家走。
“卡波妮,我知道汤姆· 鲁宾逊在监狱里,我也知道他做了很不好的事儿,可是为什么没人雇用他的妻子呢?”我问。
卡波妮那天身穿深蓝色的纱裙,戴着一顶盆形帽子,走在我和杰姆中间。“是因为人们传言汤姆干了那种坏事儿,”她说,“大家都不想——和他们家有任何牵连。”
“卡波妮,他到底做了什么?”
卡波妮叹了口气。“老鲍勃· 尤厄尔告他强奸了自己的女儿,让人把他抓起来关进了监狱……”
“尤厄尔先生?”我的记忆活跃起来,“他是不是和尤厄尔家有关系?那家人的孩子每年开学只来一天,然后就再也不来了。对了,阿迪克斯说他们是十足的无赖——我从来没听阿迪克斯这样说过谁。他说……”
“没错,他们是一家人。”
“噢,如果梅科姆所有的居民都知道尤厄尔家是些什么样的人,那大家就愿意雇用海伦了……卡波妮,什么是强奸?”
“这种事情你得去问芬奇先生,”她回答道,“他解释得比我清楚。你们俩都饿了吧?塞克斯牧师今天上午拖了好长时间,他平常可没这么啰唆。”
“他跟我们的传道人一样,”杰姆说,“不过,你们为什么那样唱赞美诗?”
“你是说‘逐行领读’?”她问。
“是这么叫吗?”
“嗯,就叫‘逐行领读’。从我记事起大家就是这么做的。”
杰姆说,他们如果把一年的善款积攒起来,也许就能买一些唱诗本。
卡波妮哈哈大笑起来。“那也没用,”她说,“他们全都不识字。”
“不识字?”我表示诧异,“所有那些人?”
“没错,”她说,“首购教会大概只有四个人除外,其余的人都不识字……我就是那四个人中的一个。”
“你在哪儿上的学,卡波妮?”杰姆问。
“哪儿也没上过。让我想想看,是谁教会我认字母的。对了,是莫迪小姐的姑姑,老布福德小姐……”
“你有那么老吗?”
“我甚至比芬奇先生年纪都大呢。”卡波妮咧嘴笑了起来,“不过,也搞不清楚到底大多少。有一次,我们回忆小时候的事情,想推算出来我究竟有多大岁数——跟他相比,我能记起来的事儿也就早几年,所以我也比他大不了太多,不过还得考虑到男人没有女人记性好。”
“卡波妮,你的生日是哪天?”
“我就把圣诞节当作生日啦,这样也好记——到底是哪天我真不知道。”
“可是,卡波妮,”杰姆提出了异议,“你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像阿迪克斯那么老。”
“黑人不怎么显老。”她说。
“也许是因为他们不识字。卡波妮,是你教会泽布认字的吗?”
“没错,杰姆先生。他小时候连学校都没有呢。不过我还是让他学会了认字。”
泽布是卡波妮的大儿子。如果我想到这一点,就应该意识到卡波妮已经上了年纪,因为就连泽布都有了几个半大孩子,可是我竟然从没想过。
“你也是用识字课本教他的吗,就跟我们一样?”我问。
“不是,我让他每天学一页《圣经》。我还有一本书,是布福德小姐教我识字的时候用的,你们恐怕猜不出来我是从哪儿得到的。”她说。
我们没有一点儿头绪。
卡波妮说: “是你们的爷爷老芬奇先生送给我的。”
“你在芬奇庄园待过吗?”杰姆问道,“你从来没跟我们提起过。”
“当然啦,杰姆先生。我那会儿在布福德庄园和芬奇庄园之间来回跑,就这么长大了。那时候,我一天到晚,不是给芬奇家干活儿,就是给布福德家干活儿。你们的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我就一起搬到了梅科姆。”
“那是本什么书呢,卡波妮?”我问。
“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
杰姆惊得瞠目结舌。“你是说,你用这本书教泽布认字?”
“噢,是啊,先生,杰姆先生。”卡波妮羞怯地用手掩住了嘴,“那是我仅有的两本书。你爷爷说,布莱克斯通先生写的英文很精彩……”
“难怪你和其他人说话不一样。”杰姆说。
“其他什么人?”
“其他黑人。不过,卡波妮,刚才在教堂里,你说话跟他们一个腔调……”
我从没想到过,卡波妮其实一直非常低调地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一想到她在我们家以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我就觉得很新奇,更不要说她还能使用两种语言了。
“卡波妮,”我问,“为什么你对——对和你一样的人说黑人话?你明明知道那不标准。”
“怎么说呢?首先,我是个黑人……”
“那并不代表你非得用那种腔调说话啊,你本来可以说得更好。”杰姆说。
卡波妮把帽子抬开一点儿,挠了挠头,又小心地把帽子压到耳朵上方。“这很难说得清楚,”她开口道,“假如你和斯库特在家里说黑人话,是不是有点儿怪里怪气?反过来看,如果我在教堂里和邻居们说白人话,会怎么样呢?他们会认为我在装腔作势,连摩西也不放在眼里。”
“可是,卡波妮,你本来能说得更好啊。”我说。
“一个人没必要把自己懂的东西都展现出来。这不是淑女的做派——再说了,人们不喜欢他们身边有什么人比他们懂得多。这会让他们气不打一处来。你使用的语言再标准,也改变不了他们。除非他们自己想学,否则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你要么闭上嘴巴,要么跟他们说一样的话。”
“卡波妮,我什么时候能去看你吗?”
她低下头注视着我说: “宝贝儿,你要看我?你每天都能看到我啊。”
“是去你家,”我说,“等哪天你干完活儿以后,行不行?阿迪克斯可以去接我。”
“你什么时候想去都行。”她满口答应了,“我们会很欢迎你的。”
这时候,我们正走在拉德利家旁边的人行道上。
“你们瞧那边廊上。”杰姆说。
我朝拉德利家望去,本以为能看到这座房子的幽灵主人坐在秋千架上晒太阳。可是秋千架上空无一人。
“我是说我们家廊上。”杰姆又说。
我顺着街道望过去,只见亚历山德拉姑姑坐在摇椅上,衣着严整,身姿笔直,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仿佛天天都坐在那里一般。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