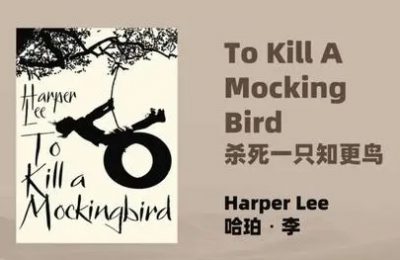《杀死一只知更鸟》是美国女作家哈珀·李发表于1960年的长篇小说。成长总是个让人烦恼的命题。成长有时会很缓慢,如小溪般唱着叮咚的歌曲趟过,有时却如此突如其来,如暴雨般劈头盖脸……三个孩子因为小镇上的几桩冤案经历了猝不及防的成长——痛苦与迷惑,悲伤与愤怒,也有温情与感动。这是爱与真知的成长经典。《杀死一只知更鸟》获1961年普利策奖。美国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书,英国青少年最喜爱的小说之一。美国中学推荐课外读物。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获第25届奥斯卡三项大奖。美国电影协会评选的“100名银幕英雄与恶人”中,派克主演的芬奇律师名列英雄第一位。作为史上最受喜爱的小说之一,《杀死一只知更鸟》已获得显赫声誉。它赢得过普利策奖,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售出超过三千万册,并曾被拍成,备受欢迎的电影。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没完没了地在杰姆耳边唠叨,他终于不再固执己见,我们的演出暂缓下来,这让我松了口气。不过,他还是坚持认为,阿迪克斯并没有制止我们演下去,因此我们就可以照演不误;即使阿迪克斯明说了,他也可以想法子糊弄过去:只要把剧中人物的名字改改,就不会被指责是在搞什么名堂了。
迪尔真心实意地赞同这个行动计划。他现在已经成了个面目可憎的讨厌鬼,整天跟在杰姆屁股后面转悠。今年夏天,他一开始还向我求过婚,可一转眼就抛在了脑后。那时候他追着我死缠烂打,把我当作他的私有财产,说我是他这辈子爱上的唯一的女孩,可后来就对我视而不见了。我揍过他两次,但毫无作用,反倒让他跟杰姆更亲密了。他们俩一天天待在树屋里,又是编造剧情又是制订计划,只有在需要第三个人出现的时候才叫上我。不过,我那段时间有意不和他们搅和在一起搞那些个鲁莽的方案,再加上被他们叫作“女孩”让我很烦恼,那个夏天后来的黄昏时分,我大多是和莫迪小姐一起坐在她家的前廊上消磨过去的。
我和杰姆一直以来都可以在莫迪小姐家的院子里随心所欲地跑来跑去,只要我们不碰她种的杜鹃花就万事大吉,但我们和她的关系并没有清楚地界定下来。在杰姆和迪尔把我踢出他们的计划之前,她只是街坊邻居中的一位女士,不过比一般人慈爱一些罢了。
我们和莫迪小姐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我们俩尽可以在她家的草坪上玩耍,吃她栽种的葡萄,但不能跳到藤架上,而且还能在她家房后那一大块地盘上随意进行探索活动。约束条款如此宽松,我们都很少跟她搭话,只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我们之间微妙平衡的关系,但杰姆和迪尔的做法无形中促使我和她拉近了距离。
莫迪小姐讨厌她的房子,在她看来,待在屋子里无异于虚掷光阴。身为寡妇的她是个变色龙一样的女人:在花坛里干活儿的时候,她头戴一顶旧草帽,身穿男式工作服,可等到下午五点钟她洗过澡之后再出现在门廊上时,她呈现出的那种凛然的美貌能征服一整条街。
她热爱大地上生长的一切,连杂草也包括在内。但有一个例外:如果她在自家院子里发现一株香附子,那简直就像是马恩河战役再一次上演。只见她拿来一只锡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扣上去,然后用一种有毒物质从底下猛喷一气。据她所说,这种除草剂威力无比,如果我们不躲开的话,会连我们也一并杀死。
“您干吗不直接拔掉呢?”我目睹了她对那株不到三英寸长的小草发动猛攻的全过程,不禁发出疑问。
“拔掉?!孩子,拔掉?!”她伸手捡起那棵蔫了的小草,用拇指捻了捻细弱的草茎,微小的草籽从里面掉了出来。“明白了吧,一棵小小的香附子就能毁掉整个院子。你瞧瞧这个,等到秋天干了之后,风一吹它们能散播到整个梅科姆县!”莫迪小姐神情严峻,就像是发生了一场《旧约》中描述的大瘟疫。
她说起话来干脆利落,不像是个梅科姆县人。她总是用全名称呼我们,咧嘴一笑就会露出镶嵌在犬牙上的一对小小的金色尖头。我对此艳羡不已,说希望将来自己也能装上几个。她说: “你看这个。”只听她的舌头发出咔嗒一声,整副假牙弹了出来。这个热诚的举动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每当杰姆和迪尔停下他们热衷的把戏,莫迪小姐的慈爱也会惠及他们俩。莫迪小姐有一项才华让我们颇为受益,她以前一直在我们面前深藏不露——那就是她做的蛋糕在街坊邻居中无人可比。当我们把她当作自己人之后,她每次烤蛋糕都会做一个大的外加三个小的,然后隔着街道冲我们大喊: “杰姆· 芬奇,斯库特· 芬奇,查尔斯· 贝克· 哈里斯,快来吧!”我们要是跑得快,往往还能得到奖赏。
夏天的黄昏悠长而宁静。我和莫迪小姐常常默不作声地坐在她家的前廊上,看夕阳慢慢落下,天空由金黄变成粉红,看一群群紫燕低低地掠过我们这片屋舍,消失在学校的一排排屋顶后面。
一天晚上,我问她: “莫迪小姐,您觉得怪人拉德利还活着吗?”
“他的名字叫阿瑟,他还活着。”她坐在自己的大橡木摇椅上慢慢地摇荡着说,“你闻见我的含羞草花了吗?今晚闻起来就像是天使的呼吸。”
“嗯,我闻到了,夫人。您是怎么知道的?”
“知道什么,孩子?”
“那个怪——阿瑟先生还活着?”
“多恐怖的问题。不过我看这本来就是个恐怖的话题。琼· 露易丝,我知道他还活着,因为我还没见他被人抬出来。”
“也许他已经死了,他们把他塞进了烟囱里。”
“你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
“是杰姆说的,他觉得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啧——啧——啧。他和杰克· 芬奇越来越像了。”
莫迪小姐和我叔叔,也就是阿迪克斯的弟弟杰克· 芬奇从小就认识。他们俩年纪相仿,一起在芬奇庄园长大。莫迪小姐是相邻庄园的主人——弗兰克· 布福德医生的女儿。布福德医生从事医药行业,但他却痴迷于大地上生长的万物,所以他一直都过着穷巴巴的日子。杰克叔叔在纳什维尔经营窗台花坛的生意,他把全部激情都投入了这桩买卖,埋头苦干,一直都很有钱。我们每年圣诞节都能见到杰克叔叔,他每个圣诞节都扯着嗓子朝住在街对面的莫迪小姐喊话,让她过来嫁给他。莫迪小姐也会喊着回答: “杰克· 芬奇,大声点儿,让邮局里的人也听见,我都还没听到呢。”我和杰姆认为,用这种方式向一位女士求婚很不可思议,不过杰克叔叔一向是个不可思议的家伙。用他的话来说,他只是想激怒莫迪小姐,可他一连尝试了四十年都没能得逞。他说他是莫迪小姐在这个世界上最不想嫁的人,也是她最想嘲弄的人,他最好的防御手段就是给她来点儿精神刺激。他这番话我们俩倒是听得十分透彻明白。
“阿瑟· 拉德利只是待在屋子里不出来罢了,仅此而已。”莫迪小姐说,“如果你不想出门的话,是不是也会待在家里呢?”
“是的,夫人。可我还是想出来啊,他为什么不愿意出门?”
莫迪小姐的眼睛眯了起来。“咱们都听说过那个故事。”
“可我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没人跟我提起过。”
莫迪小姐重新安好假牙,说: “你要知道,老拉德利先生是个行洗脚礼的浸信会教徒……”
“你也一样,对吗?”
“孩子,我可没这么死忠。我只是个普通的浸信会教徒。”
“你们不都是行洗脚礼的吗?”
“没错,用的是家里的浴缸。”
“可这样我们就不能和你们一起领圣餐了……”
莫迪小姐显然认为原始的洗礼比特权圣餐制更容易解释清楚,于是她对我说: “行洗脚礼的浸信会教徒把一切享乐都当作罪恶。你知道吗?有一个星期六,有几个他们的人从树林里走出来,经过我家院子的时候对我说,我和我种的花都会下地狱。”
“你的花也会下地狱?”
“是啊。它们会和我一起遭受烈火的煎熬。那些人觉得我把太多的精力花在户外活动上,没有拿出足够的时间坐在屋子里读《圣经》。”
我眼前不由得浮现出莫迪小姐在清教徒们所说的各种地狱里备受煎熬,永远不得解脱的情景,这让我对《福音书》的信心大打折扣。说实在的,莫迪小姐说话一向尖酸刻薄,也不像斯蒂芬妮小姐那样挨家挨户去行善积德。不过,虽然稍微有点儿脑子的人都会对斯蒂芬妮小姐打个问号,但我和杰姆却对莫迪小姐备感信任。她从来不告我们的状,从来不和我们玩猫捉老鼠的把戏,对我们的私事儿也没有半点儿兴趣。她是我们的朋友。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怎么会身陷地狱之苦,永世不得翻身呢?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莫迪小姐,这不公平。你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
莫迪小姐粲然一笑。“谢谢你。问题在于,行洗脚礼的浸信会教徒认为女人本身就是罪恶。你要明白一点,他们是按字面意义理解《圣经》的。”
“阿瑟先生闭门不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为了躲开女人?”
“我不知道。”
“我看这一点儿都不合情理。我觉得,如果阿瑟先生渴望上天堂,他至少应该从屋里走出来,在前廊上待一待。阿迪克斯说,上帝爱世人,就像世人爱自己一样……”
莫迪小姐停下摇椅,口气变得生硬起来。“你太小了,还不能理解这些事情。”她说,“有时候,某个人手里的《圣经》比有些人——比如说你父亲——手里的威士忌酒瓶还要糟糕。”
我大为惊骇。“阿迪克斯从来不喝威士忌。”我说,“他这辈子连一滴酒都没沾过——哦,不对,他喝过。他说他尝过一次,但是并不喜欢。”
莫迪小姐哈哈大笑。“我不是在说你父亲。”她解释道,“我的意思是,即使阿迪克斯· 芬奇喝得烂醉如泥,也不会像某些人神志最清醒的时候那么狠毒。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类人,他们——他们只顾担心来世,根本不去学习在今生如何做人。你顺着街道看过去,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你觉得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吗?他们说的那些关于怪——阿瑟先生的事情?”
“都是些什么事?”
我告诉了她。
“这里面有四分之三是黑人胡编乱造的,另外四分之一是斯蒂芬妮· 克劳福德的谣言。”莫迪小姐冷冷地说,“斯蒂芬妮· 克劳福德有一次还对我说,她半夜醒来,发现他正趴在窗口盯着她。我对她说,斯蒂芬妮,你是怎么做的呢?是不是在床上挪一挪,给他让个地儿?这下子让她闭嘴了一段时间。”
我相信这句话的作用。莫迪小姐的声音足以让任何人闭嘴。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孩子。”她说,“那是一座令人悲哀的房子。我记得阿瑟· 拉德利小时候的模样。不管别人说他做了什么,他跟我说话总是很有礼貌,尽可能做到彬彬有礼。”
“你觉得他疯了吗?”
莫迪小姐摇摇头。“即使他原来没疯的话,现在也差不多了。别人经历的事情,我们永远也无法明了。谁知道家家户户紧闭的大门里一天天在发生什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阿迪克斯对我和杰姆在院子里是什么样,在屋子里也什么样。”我感觉自己有责任为父亲辩护。
“好孩子,我只是在剥茧抽丝,把事情给你说个明白罢了,压根儿就没把你父亲考虑在内。不过现在我要说,阿迪克斯· 芬奇在自己家里跟在外面是一样的。你想带点儿磅糕回去吗?”
我当然乐意得很。
第二天早晨,我一觉醒来,发现杰姆和迪尔正在后院聊得起劲儿。像往常一样,我刚一凑过去,他们就让我走开。
“我就不走。告诉你,杰姆· 芬奇,这院子也有我的份儿。我跟你有同样的权利,可以随便在这儿玩。”
迪尔和杰姆立刻凑在一块儿嘀咕了几句,然后又转向我。“你要是想留下,就得照我们说的做。”迪尔向我发出警告。
“啊——哈!”我说,“是谁突然变得这么趾高气昂啦?”
“要是你不答应照我们说的做,我们就什么也不告诉你。”迪尔继续摆架子。
“你这架势,就像是一夜之间长高了十英寸似的!好吧,什么事儿?”
杰姆用平静的语调说: “我们打算给怪人拉德利送个信儿。”
“怎么送?”我极力压抑着涌上心头的恐惧。莫迪小姐随便怎么说都无所谓——她年纪大了,每天舒舒服服地待在自家前廊上,可我们就不一样了。
原来,杰姆只不过是要把一封信穿在鱼竿上,然后把它捅进百叶窗里去。如果有人从旁边经过,迪尔就赶紧摇铃。
迪尔抬起了右手——他手里拿着我妈妈的银餐铃。
“我这就绕到房子的侧面去,”杰姆说,“我们昨天已经从街对面侦察过了,那里有一片窗叶松了。我觉得,也许我至少能把信杵到窗台上。”
“杰姆……”
“你现在已经入伙了,不能临阵脱逃,你只能跟我们一起参加行动,娇小姐!”
“好啦,好啦,不过我可不想放哨。杰姆,有人……”
“不行,你必须放哨。你负责盯着房后,迪尔负责监视房前和街道,如果有人走过来他就摇铃,明白了吗?”
“那好吧。你给他写了什么?”
迪尔说: “我们非常礼貌地邀请他抽空出来,告诉我们他在屋里都干些什么——我们还说,我们不会伤害他的,而且会给他买个冰激凌。”
“你们简直是疯了,他会杀了我们的!”
迪尔说: “这是我的主意。我猜想,如果他出来跟我们坐一会儿,也许会感觉好些。”
“你怎么知道他感觉不好?”
“这个嘛,如果你被关上一百年,除了猫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吃,你会感觉怎样?我敢说,他胡子都长到这儿了……”
“跟你爸爸一个样?”
“我爸爸没有胡子,他……”迪尔突然煞住话头,像是在回想什么。
“啊哈,露馅儿了,”我说,“你原先净是吹牛,说你怎么一个人下火车,还有你爸爸留着黑胡子……”
“他去年夏天把胡子刮掉了,这下你没话说了吧!对了,我有封信可以证明——他还给我寄了两美元呢!”
“接着吹牛啊——我猜他还给你寄了一套骑警服吧!你怎么从来不拿出来显摆,说啊!你就接着吹吧,小子……”
迪尔· 哈里斯吹起牛来真是天花乱坠。除了上面那些不着边际的吹嘘,他还号称自己乘坐过十七次邮政飞机,去过新斯科舍,见过大象,他的爷爷是陆军准将约瑟夫· 惠勒,还留给了他一把宝剑。
“你们俩都给我住嘴。”杰姆说。他一溜烟儿窜到房子的台基底下,拿了一根黄竹竿钻出来。“你们看够不够长,能从人行道上伸过去吗?”
“有种走过去摸那房子,就不该用钓鱼竿。”我说,“你干吗不直接把门给踹倒?”
“这——是——两回事儿,”杰姆说,“我得告诉你多少遍才行呢?”
迪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杰姆,然后我们仨提心吊胆地朝那座老房子走去。迪尔在房子正前方的路灯柱旁边停下来守在那里,我和杰姆拖着无比缓慢的步子来到和房子平行的人行道上。杰姆立定之后我又朝前走了几步,站在可以瞧见拐角那头的地方。
“平安无事,”我报告说,“一个人影儿也看不见。”
杰姆又把目光投向人行道另一端的迪尔,迪尔冲他点了点头。
杰姆将那封信穿在鱼竿顶端,把鱼竿伸过院子,伸向他选好的那扇窗户。只可惜竿子短了几英寸,不够长,杰姆拼命向前探身。我看他一个劲儿地戳,折腾了好半天,就离开自己的岗哨向他走去。
“怎么就是弄不下来呢,”他咕咕哝哝地说,“就算是弄下来了,它在那儿也放不住。斯库特,你赶快回街上去。”
我回到自己的岗哨上,盯着拐角那头空无一人的街道,时不时回头看一眼杰姆,他还在那里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努力把信送到窗台上。可那封信老是飘落在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信戳起来再试,最后弄得一塌糊涂,我觉得怪人拉德利即使拿到信也根本没法读了。我正朝街上张望,突然听见铃声大作。
我吓得耸起肩膀,哆哆嗦嗦地转过身,准备面对怪人拉德利和他那血淋淋的尖牙;出乎意料的是,我看到迪尔正对着阿迪克斯的脸拼命摇铃。
杰姆看上去那么狼狈,我都不忍心对他说我早就警告过他了。他一步一挪地走过来,在人行道上拖着那根竹竿。
阿迪克斯说了声: “别再摇铃了。”
迪尔赶紧抓住铃锤,接下来是一阵静默,我真希望他再把餐铃摇起来弄出点儿声响。阿迪克斯把帽子推到脑后,双手叉腰。“杰姆,”他开口说道,“你们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
“别跟我绕圈子。说吧。”
“我——我们只是想把一件东西送给拉德利先生。”
“你们想送给他什么?”
“只是一封信。”
“给我看看。”
杰姆递上那张脏乎乎的纸片。阿迪克斯接过来,费劲儿地读了起来。“你们为什么想让拉德利先生出来?”
迪尔答道: “我们觉得,他可能会喜欢和我们在一起……”阿迪克斯瞟了他一眼,他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儿子,”阿迪克斯对杰姆说,“你好好听着,这话我只跟你说一遍:别再去折磨那个人了。还有你们两个。”
拉德利先生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他想走出家门,他就会出来。如果他想闭门不出,他也有权利待在屋子里,避开那些喜欢追根究底的孩子。“喜欢追根究底的孩子”用在我们这种人身上算是个客气的说法。假如我们晚上待在自己房间里的时候,阿迪克斯不敲门就闯进来,我们会高兴吗?实际上,我们刚才对拉德利先生所做的一切就等于是不速之客贸然闯入。拉德利先生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眼里可能很古怪,但在他自己看来一点儿都不出格。再说了,我们脑子里难道没有闪过一丝念头,根本没有想到与人交往的体面做法是走前门,而不是通过侧面的窗户吗?最后他明令禁止我们再靠近那座房子,除非受人之邀;不许再演那出愚蠢的戏——上次他就把我们抓了个正着;也不许取笑住在这条街上或者住在这个镇子上的任何人……
“我们没有取笑他,也没有嘲弄他……”杰姆说,“我们只不过……”
“这么说,你们一直都在忙活这个,是不是?”
“取笑他?”
“不,”阿迪克斯说,“你们把他的个人经历编进戏里表演给街坊邻居看,让大家从中受到启发。”
杰姆似乎有点儿沾沾自喜: “我并没有说过我们演的是他呀,我没有说过!”
阿迪克斯冷冷地一笑。“你刚刚已经告诉我了。”他说,“从现在起,不准再胡闹,你们每个人都包括在内。”
杰姆望着他,目瞪口呆。
“你不是想当律师吗?”我们的父亲阿迪克斯把嘴唇闭得紧紧的,抿成了一条线,我真怀疑他是在强忍着笑,故作严厉。
杰姆沉默不语,因为他知道狡辩是毫无用处的。阿迪克斯进屋去拿他早晨上班时忘带的卷宗,这时候,杰姆才如梦初醒:自己原来中了有史以来最古老的律师圈套。他恭恭敬敬地站在那儿,与前门台阶拉开一段距离,看着阿迪克斯离开家门,向镇上走去。等他料定阿迪克斯听不见了,才冲着他的背影大声喊道: “我原以为自己想当个律师,可现在我没那么肯定了!”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