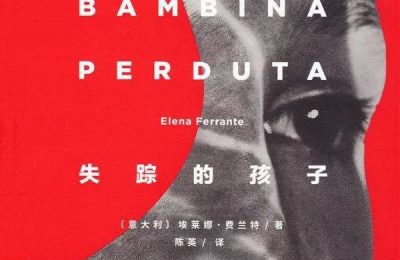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我不知道她在多长时间里一直相信她女儿还活着。恩佐越是绝望哭泣,越是愤恨,莉拉就越说:“你看吧,他们会把孩子还回来的。”她从来都不相信是那辆卡车肇事逃走。她说,如果事情真是那样,她一定会马上察觉的,她一定会比任何人更早听到撞击声或者叫喊。我觉得,她也不赞同恩佐的看法,她从来都没有说孩子丢了的事儿和索拉拉兄弟有关。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她认为是她的一个客户把蒂娜带走了,因为他知道“Basic Sight”的经营情况,他一定是想要让他们用钱把孩子赎回去。这也是安东尼奥的看法,不知道有什么具体的依据。警察当然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接到要钱的电话,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城区里的人持有两种观点,大部分人认为蒂娜已经死了,小部分人认为她被关在了某个地方,我们这些爱莉拉的人属于少数派。卡门非常肯定这种可能,她遇到谁都会这样说,假如有人认为蒂娜死了,那就会成为她的敌人。我听见她有一次对恩佐说:“你告诉莉娜,帕斯卡莱和我们想法一样,他觉得孩子一定能找到的。”但大部分人不那么认为,他们觉得那些继续寻找蒂娜的人,要么很蠢,要么很虚伪。他们对于莉拉的看法也变了,觉得她的脑子帮不了她。
卡门是第一个意识到:在蒂娜失踪之前人们对莉拉的支持,以及孩子失踪之后大家对她的安慰,都是非常表面的,在这些安慰和支持下面是对她根深蒂固的讨厌。她对我说:“你看,以前人们都觉得她像圣母一样,现在他们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就过去了。”我也开始注意到这一点,我意识到事情真是这样的。人们内心深处一定是这么想的:蒂娜丢了,我们也很难过,但这意味着,假如你真是你之前表现的那么有能耐,那肯定没人敢碰她的。我们一起走在路上,人们开始跟我而不是跟她打招呼。她那副心神不安的模样,还有遭遇不幸的惨淡让人很担忧。总之,城区里那些以前认为莉拉可以取代索拉拉兄弟的人也失望地退缩了。
不仅仅如此,刚开始几天人们的善意举动,后来充满了恶意。在她家大门口,在“Basic Sight”门口,刚开始几个星期出现了一些写给莉拉,或者是写给蒂娜的纸条,甚至是一些从课本上抄的诗歌,后来开始有一些妈妈、奶奶和孩子送来的玩具、发卡、彩色的皮筋,还有穿过的鞋子,最后出现了手工缝制的表情很可怕的娃娃,上面有红色的墨水,还有一些包在肮脏的破布里小动物的尸体。莉拉静静地把每样东西都捡了起来,扔到了垃圾桶里,但忽然间,她开始叫喊,大声咒骂经过那里的任何人,尤其是骂那些从远处看着她的小孩子,她从一个让人同情的母亲,变成了一个让人害怕的疯子。有一次莉拉狠狠骂了一个女孩,那个女孩用粉笔在门上写了一句:“蒂娜被鬼吃了。”后来这个女孩得了重病,之前关于莉拉的那些谣传又回来了,就好像看她一眼都会带来不幸。
她自己好像没觉察到这一点,她确信蒂娜还活着,她全身心地相信这一点,这把她推向了伊玛。在开始几个月,我尽量减少我的小女儿和她的接触,我担心莉拉看见她会更加痛苦,但莉拉不停地想要伊玛和她待在一起,假如我允许,她让孩子晚上也睡在她家里。有一天早上,我去她家接伊玛,门虚掩着,我就进去了,孩子正在问蒂娜的事儿。在那个星期天蒂娜出事儿之后,为了让伊玛平静下来,我一直都跟她说,蒂娜去了阿维利诺恩佐一个亲戚家了,但她会一直追问,蒂娜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现在,她直接问莉拉,但莉拉好像没听到伊玛的声音,她没回答,而是仔细说起了蒂娜出生时的事儿,她的第一个玩具,还有她吃奶时很投入根本停不下来,诸如此类的事儿。我在门槛那里听了几秒钟,我听见伊玛忽然很不耐心地打断了她,问:
“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觉得孤单啊?”
“我不知道和谁玩儿。”
“我也一样。”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莉拉有很长时间都没说话,然后开始责备伊玛。
“你不要问了,那不是你管的事儿。”
这样的话用方言说出来,听起来是那么粗暴,那么尖刻和不合时宜,这让我很不安。我和她泛泛聊了几句,就把我女儿带回家了。
我一直原谅莉拉做的那些过分的事儿,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比过去更倾向于原谅她。她经常很夸张,我尽量体谅她。警察在审讯斯特凡诺时,她马上确信蒂娜是他带走的。在斯特凡诺心脏病发作后有一段时间,她拒绝去医院看他,我开导了她,跟她一起去看了她前夫。警察在审讯里诺时,她没把这事怪在她哥哥身上,那也是我的功劳。在她儿子詹纳罗被叫去警察局的可怕的那天,我也全力缓和他们的关系,詹纳罗回到家里,感觉自己受到了委屈,他和莉拉吵了一架,然后去他父亲家里住了。他对莉拉说,她不但永远失去了蒂娜,也永远失去了他这个儿子。总之,情况非常糟糕,我明白,她生所有人的气,包括我。但她不能生伊玛的气,她没这个权力。从那时候开始,当莉拉把伊玛带走时,我会为此焦虑,我会想办法,想找到解决的方案。
但没办法,她的痛苦已经缠绕成一团,伊玛是这团乱麻的一部分。总的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卷入其中,莉拉尽管很崩溃,还是一直跟我说我女儿的每个小问题,我后来不得不决定让尼诺来家里。我感觉到她的顽固,这让我很恼火,但我尽量让自己看到事情好的一面:她慢慢把她的母爱移到了伊玛身上。我想,她要对我说的是:你看你多幸运,你女儿还在,你应该好好珍惜,关心她,好好照顾她。
但这只是表面。我很快有了一个不同的推测,在莉拉内心深处,伊玛在她看来应该是她内疚感的象征。我经常想着孩子丢失的情景,尼诺把孩子交给了莉拉,但莉拉没有看好自己的女儿。当时她可能对孩子说:“你在这儿待着。”然后跟我女儿说:“你跟阿姨来。”也许她这么做,是想把伊玛放在她父亲眼皮底下,是想在他面前赞扬她,激发尼诺的情感,谁知道呢。但蒂娜很活跃,或者她觉得自己被忽视了,生气地走远了。结果是那种痛苦和伊玛在她怀里的感觉——一种活生生的热度联系在一起了。但我女儿脆弱、迟钝,她和蒂娜截然不同,蒂娜是那么聪慧灵巧。伊玛无论如何都不能取代蒂娜,她只是对抗时间的一道堤坝。我想象着,莉拉让伊玛在她跟前,就是想让时间停留在那个可怕的星期天,她会想着:蒂娜马上会回来,她一会儿就会拽着我的裙子,会叫我,我就会把她抱起来,一切都恢复到之前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她不愿意伊玛打乱任何东西的原因,当伊玛问她蒂娜什么时候出现时,当孩子让莉拉想到蒂娜不在这里时,莉拉就会变得很粗暴,她对待伊玛就好像对待我们大人一样。我没法接受这些。她来接伊玛时,我会找一个借口让黛黛或者艾尔莎跟去,看着她。如果我在场的时候,她就是用的那种语气,我不在场的几个小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