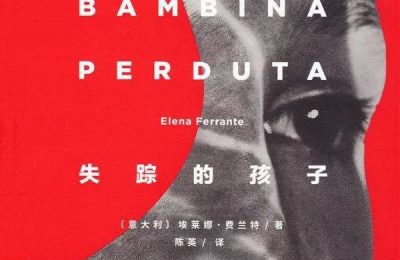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在我们的城区里,没有任何人对于执法机关和报纸抱有希望。男人、女人,甚至那些少年帮派,他们完全无视警察和电视,都在找蒂娜,找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所有亲戚朋友都发动起来了。唯一偶尔打来电话的人是尼诺,他会说一些泛泛的话,唯一的目的就是重申:“我没任何责任,我已经把孩子交给莉娜和恩佐了。”但我一点儿也不惊异,他就是那种会陪着小孩一起玩儿的大人,但孩子跌倒了,摔破了膝盖,他们也会变得和孩子一样,担心有人会对他说:“是你让孩子摔倒的。”也没人想到他,在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忘了他这个人。恩佐和莉拉最信任的人是安东尼奥,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为了找到蒂娜,他又一次推迟了去德国的时间。他这么做是因为友谊,让我们吃惊的是,他说这也是米凯莱·索拉拉交待的。
索拉拉兄弟比任何人都投入到孩子失踪的事情中。我不得不说,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做做样子,让人们看到他们在采取行动。尽管他们知道自己不受欢迎,有一天晚上,他们还是出现在莉拉家里,他们用一种代表整个城区的语气,说他们想尽办法,尽一切努力使蒂娜完好无损地回到她父母的身边。莉拉一直都盯着索拉拉兄弟,好像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恩佐脸色非常苍白,他听他们说了几分钟,然后大声说,是他们把孩子带走了。他在其他场合也说过这样的话,他对所有人说,索拉拉兄弟把蒂娜带走了,因为他和莉拉一直拒绝给他们分公司的利润。他期望有人能提出反对,他好跟人动手,但当着他的面,没人说什么,那天晚上索拉拉兄弟也没说什么。
“我们理解你的痛苦。”马尔切洛说,“假如有人把我的西尔维奥带走的话,我也会跟你一样,会疯了的。”
他们等着有人让恩佐平静下来,然后走了。第二天,他们让各自的妻子——吉耀拉和埃莉莎——过来探望,莉拉和恩佐很冷淡地接待了她们,但并没有失礼。在这之后,他们寻找得更卖力了,可能就是索拉拉兄弟,组织人扫荡了所有通常来城区摆摊的小商小贩,还有周围所有吉普赛人的营地。当然,也是他们组织那些愤怒的民众,针对那些开着警车、鸣着警笛过来抓人的警察。他们先抓了斯特凡诺——他那个阶段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来住院了,他们还抓了里诺,但几天后就被放出来了,最后甚至是詹纳罗,他哭了好几个小时,发誓说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爱这个小妹妹,他永远都不可能伤害她。无法排除的是,索拉拉兄弟派人在小学门口守着,因为他们的缘故,那个在小学门口诱拐儿童的变态狂,才从一个道听途说的传言成了一件有理有据的事儿。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小男人,尽管没孩子要接送,但他一直出现在学校门口。他被痛打了一顿,逃走了,他被一群愤怒的人追打到了小花园那里。假如他没把话说清楚,那他肯定会被人们打死。他说,他不是人们想象的变态,他只是《晨报》的实习生,正在寻找素材。
经过那个事件之后,城区逐渐平静下来了,人们逐渐恢复了之前的生活。因为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蒂娜的线索,她被大卡车轧了的传言越来越可信了,那些厌倦于寻找的人,还有警察和记者都相信了这一点。人们的注意力放在了那个地区的工地上,那里停工已经很久了。这时候,我重新见到阿尔曼多·加利亚尼——我高中老师的儿子,他已经不再做医生了,他在一九八三年的选举中没能进入议会,现在通过一家不怎么样的私人电台在尝试一种非常尖锐的报道方式。我得知,他父亲在一年多前死了,她母亲在法国生活,身体也不怎么好。他让我陪着他去找莉拉,我跟他说,莉拉现在状态不好,但他依然坚持要去。我给莉拉打了电话,莉拉费了很大力气才想起了阿尔曼多,想起他来之后——到那时候为止,她还没和任何记者谈过——她同意见面。阿尔曼多解释说,他正在做一个地震后的报道,他在那些工地里走动时,他听说有一辆卡车被快速报废了,那是因为它卷入了一件很恶劣的事情。莉拉让他说了一会儿,然后说:
“这都是你的想象。”
“我只是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事情。”
“你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卡车、工地和我女儿。”
“你在骂我吗?”
“不,刚才不算,我现在开始骂你:你是一个很烂的医生,一个很烂的革命者,现在你是一个很烂的记者,从我家里滚出去!”
阿尔曼多的眉毛皱了起来,他跟恩佐打了一个招呼就走了。我们到了外面,他表现得很难过。他嘟囔着说:“即使是这么大的痛苦,也没能改变她,你跟她说说,我想帮助她。”他对我进行了一个非常漫长的采访,然后我们告别了。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和气的态度,还有他说话时的措辞。他应该度过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先是她妹妹娜迪亚作出的选择,后来是他和妻子分开。他看起来很精神,他之前那种对反资本主义无所不知的态度,现在变成了一种痛楚的厌世。
“意大利现在变成了一个盲井。”他用痛苦的语调说,“所有人都掉了进去,你四处看看,那些善良的人都明白了这一点。埃莱娜,真的太遗憾了,工人阶级的党派里有很多诚实正直的人,但他们都已经失去希望了。”
“为什么你要做现在这份工作?”
“和你做你的工作原因一样。”
“也就是说?”
“当我毫无遮掩时,我发现自己很虚荣。”
“谁说我很虚荣。”
“对比而言,你的朋友一点儿也不虚荣,我为她感到难过,虚荣是一种资源。假如你很虚荣,你会很小心你自己,还有你自己的东西。莉拉一点儿也不虚荣,因此她失去了女儿。”
我听了一阵子他的电台,他似乎做得很出色。他在红桥那里找到了一辆烧掉的卡车架子,他把这辆卡车和蒂娜的失踪联系在一起。这个消息引起了一阵轰动,后来出现在全国的报纸上,有一阵子,人们都在谈论这事儿。最后事情搞清楚了,这辆被烧的卡车和孩子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莉拉跟我说:
“蒂娜活着,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烂人。”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