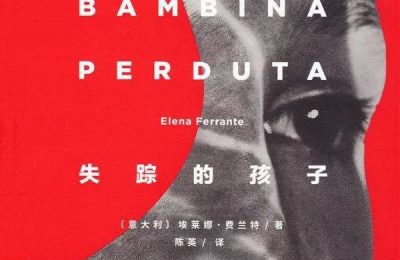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早上,主编给我打了电话,一张口就说了很多好话。
“这个阶段,你文思如泉涌啊!”他说。
“这是我和我一个朋友一起写的。”
“能看出来你的文风,但比之前更好了,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拜托你让萨拉托雷教授看看这篇文章,这样他就明白,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文采飞扬、激动人心的文字表现出来。”
“我已经不再和尼诺见面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状态才这么好。”
我没笑,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律师是怎么说的,他的回答却让我非常失望。主编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他们进监狱,哪怕是一天。但你要知道,索拉拉兄弟是很难进监狱的,尤其是就像你说的,他们已经渗透进地方政治,可以买通任何人。我觉得很虚弱,双腿发软,我失去了信心,我想莉拉一定会很生气。我有气无力地说:“他们要比我写得更糟糕。”主编感受到了我的失望,尽量想让我打起精神,他接着赞美了我在那篇文章里投入的激情。但结论还是一样:凭我手头的东西,很难把他们摧毁。最后让我惊异的是,他让我不要把那篇文章搁置起来,而是要把它发表。“我打电话给《快报》,”他提议说,“假如在这个时候你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对你、你的读者和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你向他们展示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意大利,实际上要比小说里讲述的还要糟糕。”他说,他要重新咨询一下律师,想知道如果发表这篇文章我们会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风险,需要删除或者修订什么。他想征得我的同意。我想,当时吓唬布鲁诺·索卡沃时,事情是多么简单,我很坚定地回绝了。我说:“我会又一次被起诉的,不得不陷入一大堆麻烦——出于对几个女儿的爱,我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我不得不想到,法律对于害怕它的人管用,对于打破它的人却没用。”
我等了一会儿,才打起精神去找莉拉,一字不差地跟她转达了编辑的话。她很平静,打开电脑看着那篇文章,但我觉得,她没有重读那篇文章,她在盯着屏幕思考。然后她用一种带着敌意的语气问我:
“你信任这个主编吗?”
“是的,他是个好人。”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发表这篇文章?”
“发表有什么用?”
“把事情讲清楚。”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谁清楚了?你,我,还是主编?”
她很不高兴地摇了摇头,冷冰冰地说她要工作。
我说:
“等一下。”
“我很忙。没有阿方索,这里的工作很麻烦。你走吧,拜托了,走吧。”
“为什么你要生我的气?”
“走吧。”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见面。早上,她让蒂娜自己上楼来,晚上恩佐来接她,要么她就在楼梯间大喊:“蒂娜,下来吧,妈妈回来了。”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主编兴高采烈地给我打电话了。
“很好,我很高兴你最后决定了。”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跟我解释说,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在《快报》工作的编辑,非常着急要我的联系方式。从主编那里我得知,关于索拉拉的那篇文章,在删节之后会在这个星期刊出。他说:“你应该告诉我,你改变主意了。”
我出了一身冷汗,不知道说什么,我假装若无其事。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是莉拉把我们的文章发给了那家周报。我非常气愤,跑到她那里去抗议,但她对我特别亲切,尤其是她很愉快。
“我看你没办法决定,就替你决定了。”
“我已经决定不发表这篇文章。”
“但我不是这么决定的。”
“那你只署你自己的名字。”
“你在说什么?写东西的人是你。”
我没办法让她领会我的反对,还有我的不安,我每一句批评的话都会让她心情更好。那篇文章发表了,一共六页,密密麻麻的,占了非常重要的版面,当然文章只有一个署名,是我的名字。
看到报纸时,我们吵了一架。我非常气愤地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我明白。”她回答说。
她脸上还有米凯莱的拳头留下的痕迹,她没有署名并不是因为害怕。她害怕的是别的事情,就我所知,她根本就不在乎索拉拉兄弟。但我当时很生气,忍不住对她说:“你把你的名字去掉了,是因为你喜欢藏在暗处,丢完石头藏起手,对你来说是自然而然,我已经厌烦你的伎俩了。”她笑起来了,她认为我对她的控诉没有意义。她说:“我不喜欢你这么想。”她做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说她把那篇文章发给《快报》,只署了我的名字,那是因为她的名字一点分量都没有,我是上过大学的人,我是那个有名的人,可以毫无畏惧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听到她的这些话,我确信她太高估了我的作用,就告诉了她我的想法。但她很不屑,她说我总是低估自己,因此她希望我更加努力,表现得更出色,要获得更大的认可,她一心想着我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她感叹说:“你走着瞧吧,索拉拉兄弟没什么好下场。”
我灰溜溜地回到家里。我没办法摆脱那种怀疑,就是她在利用我,就像马尔切洛说的那样。她不管我的死活,利用我的那点儿名声来打赢她的那场战争,实现她的报复,消除自己的愧疚和不安。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