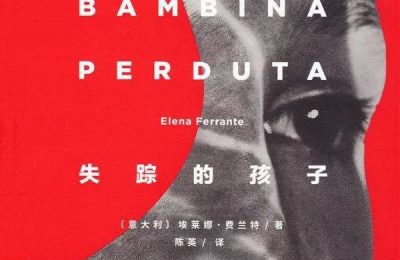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我觉得很多人都在想,一个在报纸上看起来又有钱又有名的人,为什么要搬到这套破旧的房子里住,而且这套房子位于一个越来越破败的城区。也许首先我的两个女儿就不能理解这一点。有一天早上,黛黛从学校回来,满脸嫌弃地说:
“有一个老头朝我们学校大门里尿尿。”
还有一次,艾尔莎从学校里回来,她吓得要死,说:
“今天有个人在小花园里被人用刀子捅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害怕,脱离城区已经很久的那个我很恼火,很为两个孩子担心,我在心里说:我受够这里了!在家里,黛黛和艾尔莎说一口纯正的意大利语,但有时候,我隔着窗子,或者在她们上楼梯时,能听到艾尔莎会说一口粗俗的那不勒斯方言,有时候甚至会用很肮脏的词。我会骂她,她假装很难过,但我知道,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才能抵挡说粗话还有其他的诱惑。有没有可能,我在搞文学的同时,她们迷失了?唯一给我带来安慰的是,我不会在这里住很久。我的书出版之后,我会彻底离开那不勒斯。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我只是需要等到我的小说定稿。
城区的方方面面无疑对这本书都有好处。我的工作进展得如此顺利,尤其是因为我对莉拉的关注:她全然融入了那个环境,她的声音、目光、动作,她的邪恶和慷慨,还有她说的方言,都和我们出生的这个地方紧密相连。就像她的“Basic Sight”(人们会把她的公司称为“巴西西”),尽管是一个外国名字,但它不像一块来自太空的陨石,而是这个贫穷、暴力和落后的环境的一个令人意外的产物。我从她身上汲取能量,赋予我的小说一种真实的力量,这对于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写完这本书之后,我会永远离开这里,我打算搬到米兰去住。
我在她的办公室里待上一会儿,就会意识到她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工作。我看着她哥哥,他已经完全被毒品侵蚀了。我看着艾达,她越来越凶恶,成了玛丽莎誓不两立的敌人,因为玛丽莎彻底抢走了斯特凡诺。我看着阿方索,在他的面孔和举止里,男性和女性的气质一直在打破界限,产生的结果有时候让我很恶心,有时候让我很震撼,但我越来越不安,因为他的眼睛常常是乌青的,要么就是嘴唇被打破了,总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被人打了。我看着卡门,她穿着加油站的蓝色工作服,把莉拉拉到一边询问,就好像莉拉是一个先知。我看着安东尼奥,他也围着莉拉转,有时候会说两句,有时候会待在一边不说话,他会把他漂亮的德国妻子和孩子带到莉拉的办公室去拜访她,就像是一种示好的表现。我时不时会听到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斯特凡诺·卡拉奇要彻底关掉他的肉食店,他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他想要钱;帕斯卡莱·佩卢索绑架了政治要人提兹奥,假如不是他自己动手的,也一定和他相关;阿弗拉戈拉的一家衬衣店发生火灾,是卡伊奥自己放的火,他只是想骗保险;让黛黛要小心点儿,他们会给小孩子下了药的糖果,在小学周围有一个变态在转悠,会把小孩子拐走;索拉拉兄弟要在新城区开一家夜总会,有女人和毒品,音乐声会非常大,以后晚上没人能睡着;在大路上,夜里会有一些超级大卡车经过,载着一些比核弹还可怕的东西;詹纳罗交了一些坏朋友,假如他再这样下去,莉拉就不让他出去上班了;那个在隧道里被杀死的人看起来是个女的,其实是个男的,他身上流了那么多血,一直到加油站那里都能看到。
我观察着,倾听着,充分扮演着我的角色。我和莉拉小时候想成为作家,但我现在真的成了作家。我正在修订一本重要的书,有些地方我会重写,这本书马上会出版。我想,在第一版里,我用了太多方言,我把那些方言都抹掉了,重新写,但后来我又觉得方言太少了,又加了一些。我住在城区里,还在故事的场景之中,在那些角色之间。这本充满野心的小说,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也使我完全投入其中。我赋予这里的每样事物意义:房间灰黄的灯光,路上粗鲁的叫喊,几个孩子所冒的风险,大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天气好的时候,会扬起一阵阵灰尘,下雨时会溅起泥浆,还有莉拉和恩佐的那些客户,都是小地方的一些小老板,他们开着豪车,穿得很奢华,但很庸俗,他们有时候会非常霸道地挺着肚子走来走去,有时候会点头哈腰。
有一次我和伊玛、蒂娜在一起,在“Basic Sight”等莉拉。事情变得非常明显:莉拉在做一项全新的工作,但她却完全沉浸在我们之前生活的那个世界里。我听见她为了钱的事儿用非常粗野的语言对着一个客户叫喊。我对此很震惊,那个全身都散发着权威的和气的女人去哪儿了?恩佐马上跑去察看,那个六十岁上下,个头很小,肚子很大的男人骂骂咧咧地走了。后来我问莉拉: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意思?”
“如果你不想说,那就算了。”
“不,我想和你说,但你要说清楚,你想知道什么。”
“我是想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你怎么对付那些和你打交道的人。”
“像所有人一样,我会很小心。”
“仅仅是这些?”
“好吧,我很小心,我会让事情向我希望的方向发展。我们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吗?”
“是的,但我们现在要承担责任,对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孩子。你不是说过,我们应该改变这个城区?”
“要改变城区,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要诉诸于法律。”
说出这样的话,连我自己都很惊异。我发现从某些方面来说,我的话比我前夫和尼诺的话更加冠冕堂皇。莉拉开玩笑地说:
“法律只对有些人管用,就是那些你一说‘法律’,他们就会马上很小心的人,但你知道这里的情况。”
“然后呢?”
“假如人们不害怕法律,你应该让他们感到害怕。你刚才看到的那个混蛋,我们为他做了很多工作,非常多的工作,但他不想给钱,他说他没钱。我威胁了他,我对他说:‘我会去告你。’他回答说:‘你去告啊,谁他妈在乎。’”
“你会去起诉他吗?”
她笑了起来:
“这样我永远都见不到我的钱了。之前有一个会计师,偷了我们好几百万里拉。我们把他开除了,告上法庭了,但法律并没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呢?”
“我等得很心烦,就把安东尼奥叫来了,那些钱马上就回来了。这次的这些钱也会回来的,不用打官司,不用律师和法官。”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