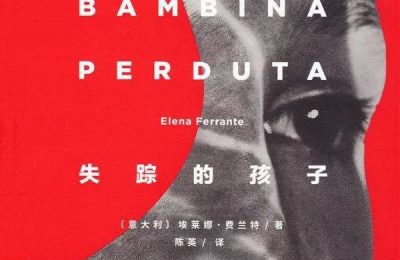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我在盛夏时换了房子,是安东尼奥帮我搬的家。他找了一些强壮的男人,把塔索路上的房子腾空,把东西都搬到城区的房子里。新房子光线很暗,即使把房间重新刷过,也没能让它明亮起来。我现在的想法和刚回那不勒斯时的想法完全相反,这样的生活环境没有让我不悦,对于我来说:从旧楼窗户里透进来的黯淡的光,让我想起了童年的生活,我感觉很温馨。但黛黛和艾尔莎抗议了很长时间,她们是在佛罗伦萨、热内亚,还有塔索街上那些宽敞明亮的房子里长大的,她们马上就开始抗议地上坑洼不平的地砖,又小又黑的洗手间,大路上的喧嚣。她们后来接受了现实,那是因为住在这里也有很多好处:每天见到莉娜阿姨,学校很近,可以不用很早起床去学校,自己去学校,不用人送,可以在外面街上和院子里待很久。
我马上就重新融入城区。我给艾尔莎注册了我之前读的小学,让黛黛就读我之前读过的初中。我跟所有人都重新建立起了联系,老的少的,只要他们还记得我。我和阿方索、艾达、皮诺奇娅、卡门还有她的家人一起庆祝我搬回来的决定。我有些担心彼得罗的反应,自然,他对于我的这个选择很不满意,他跟我明确说了他的看法。他打电话对我说:
“你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则,让我们的女儿在一个你逃离了的地方长大?”
“我不会让她们在这里长大。”
“但你在那里租了房子,你给她们注册了那里的学校,你没有想过她们应该过更好的生活。”
“我要完成一本书,只有在这个地方,我才能写出来。”
“你可以让她们和我一起生活啊。”
“你也会让伊玛和你在一起生活吗?她们都是我的女儿,我不想让伊玛和她的两个姐姐分开。”
他平静下来了。他很高兴我离开了尼诺,所以很快就原谅了我搬家的事情。他说:“你好好写东西,我相信你,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希望他说的是真的。我望着大路上来来往往的卡车,它们发出巨大的声响,扬起阵阵灰尘。我在小花园里散步,看到到处都是针管。我进到空荡荡、被人们忽视的教堂。我走在已经关闭了的教区电影院门口,各个党派的支部办公室也好像被遗弃的洞穴,我感到阵阵悲伤。我听着男人、女人和孩子在房子里叫喊,尤其是晚上,让我感到害怕的是家庭内部的冲突,邻居之间的敌意,人们一言不合就动手,还有男孩帮派之间的斗争。去药店时,我会想到吉诺,看到他被杀死的地方,我觉得毛骨悚然,我会小心翼翼地绕开那个地方,我对他的父母感到同情,他们依然站在深色的柜台后面,腰更弯、背更驼了,头发和他们的白大褂一样白,说话还是那么客气。我想,这就是我从小面对的一切,我倒要看看,现在我还能不能掌控。
“你是怎么决定回来的?”我搬到城区之后,有一天莉拉问我。也许她期待我说一些念旧的话,或者说一些对她之前的选择表示肯定的话,比如说:你选择留在这里是对的,现在我明白了,去世上闯荡也没什么用。但我回答说:
“这是一个尝试。”
“什么尝试?”
当时我们在她的办公室里,蒂娜在她跟前,伊玛在自己转悠。我对她说:
“尝试把一切重新组合起来。你能完整地生活在这里,但我不行,我感觉自己的生活支离破碎。”
她看起来很不赞同。
“莱农,别想着这些实验,否则你会失望,又会离开。我也是支离破碎的,我父亲的修鞋铺子距离我办公室只有几米远,但我感觉我们就像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
我故作轻松地说:
“不要让我泄气,我的职业就是通过语言把一件事情和另一件事情粘合起来,最后所有一切应该前后连贯,虽然事实上它们并不连贯。”
“假如不存在连贯性,为什么要假装呢?”
“就是把事情厘清。你记不记得我让你看的那本小说?你说不喜欢的那本。我想把我所知道的那不勒斯和我在比萨、佛罗伦萨和米兰学到的东西结合起来。现在我把这本书给了出版社,他们觉得这本书很好,决定出版了。”
她眯起眼睛,轻声说: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什么都不懂。”
我感觉到我伤害她了,我说那番话,就好像毫不客气地对她说:假如你不能把鞋子和计算机的故事放在一起,这就意味着你做不到,你没有必要的工具。我后来很仓促地说了一句:“你看吧,你的判断是对的,这本书不会有人买的。”我列举了这本书在我眼里的一系列缺陷,就是在出版前要修订或者决定保留的地方。但她却绕开了这个话题,开始说起了电脑,她说这些就好像为了占上风,就好像要强调:你有你的事业,我有我的。她给几个孩子说:“你们要不要看恩佐刚买的新机子?”
她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她给黛黛还有艾尔莎解释说:“这台机子叫做个人电脑,花一大笔钱买的,它可以做一些很棒的事情,你们看看,这机子怎么用。”她坐在一张凳子上,把蒂娜抱起来放在膝盖上,开始仔仔细细给黛黛、艾尔莎还有小蒂娜讲解电脑的每个部件,她从来都没对着我说。
整个过程,我都在看着蒂娜,她在和她母亲说话,指着眼前的东西问:“这是什么?”假如母亲没有理会她,她会拽着莉拉的衣角,会摸她的下巴,坚持问:“妈妈,这是什么?”莉拉会跟她解释,就好像她已经是大人了。伊玛在房间里转悠,她拽着一个有轮子的小推车,有时候会很茫然地坐在地板上。我叫了她好几次:“伊玛,你过来听听莉娜阿姨说什么。”但她还是在那里玩小推车。
我的女儿不像莉拉的女儿那么聪明。有一阵子,我一直很担忧她发育迟缓。我把她带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儿科医生那里,医生说,孩子各个方面的发育都没有问题,我才放心了。尽管如此,把伊玛和蒂娜放在一起比较,总是让我有些难受。蒂娜多活跃啊!看看她的表现,听她说话,真是让人高兴。她们母女两人在一起真是让我感动。莉拉在谈论电脑时——我们开始用“电脑”这个词——我用欣赏的目光注视着她们俩。在那种时刻,我觉得很幸福,为自己感到满意,我很清楚地感觉到,我爱我朋友本来的样子,爱她的优点和缺点,爱她所有的一切,包括她生的这个小家伙。蒂娜充满了好奇,她学东西很快,她的语言很丰富,手也很灵巧。我想,她一点儿都不像恩佐,她和莉拉一模一样,看看她瞪着眼睛,或者眯着眼睛的样子,还有她耳垂很小的耳朵,简直太像莉拉了。我不敢承认,蒂娜对我的吸引力要比我女儿大。当莉拉展示完电脑,这个新玩意让我也产生了兴趣。尽管我知道伊玛可能会难过,但我还是赞美了蒂娜:“你真聪明,真漂亮,你说话说得真好,懂的东西可真多啊!”我也说了莉拉很多好话,尤其是为了抵消我要出版那本书带来的不安。我最后为几个姑娘——我的三个女儿,还有蒂娜勾勒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我说,她们会学习,在全世界旅行,谁知道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物。莉拉在蒂娜脸上亲来亲去,有些不悦地说:“是的,她很聪明。詹纳罗以前也很聪明,很会说话,也看书,在学校里学习很好,但你看看他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