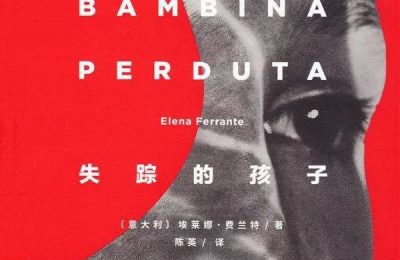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天气很冷,伊玛有生病的危险,但我觉得,我实在没法回家。我把她包在我的大衣里,就好像我们在玩游戏。我给她买了一包新尿布,用纸巾将她擦干净之后换上。现在我要决定该怎么办。黛黛和艾尔莎很快会从学校里出来,她们肚子会很饿,心情很坏,伊玛这时候已经饿了。我神经紧绷着,身上的牛仔裤是湿的,我没有大衣,冷得发抖。我找了一个电话,打给莉拉。我问:
“我能带几个孩子来你家吃午饭吗?”
“当然了。”
“恩佐不会很烦吧?”
“你知道他会很高兴的。”
我听见蒂娜在电话那边欢快的叫喊声,莉拉对她说:“别叫!”然后,她用一种少有的小心翼翼的语气问我:
“出什么事儿了吗?”
“是的。”
“怎么了?”
“就是你之前已经预料到的。”
“你和尼诺吵架了吗?”
“等下我告诉你,现在我得走了。”
我提前到了学校门口,这时候伊玛已经对我、汽车方向盘还有喇叭彻底失去了兴趣,她变得很烦躁,哭得浑身发抖。我把她紧紧包在大衣里,去给她找饼干。我相信自己的举止很正常,内心很平静,我觉得恶心,而不是愤怒,那种厌烦无异于看到了两个正在交配的蜥蜴——但我觉察到,路上的人用一种好奇的目光在打量着我,有些不安地看着我穿着一条湿漉漉的裤子,在街上奔走,大声和包在大衣里的孩子说话,孩子在挣扎哭泣。
第一块饼干就让伊玛平静下来了,但我的焦虑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尼诺可能已经推迟了他的约会,有可能正在找我,我可能会在学校门口遇到他。黛黛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艾尔莎比黛黛放学早,我在小学门口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看着那道小门。我冷得牙齿打架,伊玛把她的口水和饼干渣都弄到了我的大衣上了。我很警惕地看着那个区域,但尼诺没有出现。他也没有出现在中学校门口,这时候,黛黛很快在推推搡搡的人群操着方言的骂声和叫喊声中走了出来。
两个孩子都没有太关注我,她们只是对我带着伊玛去接她们表示好奇。
“你为什么要把她包在大衣里?”黛黛问。
“因为她很冷。”
“你有没有看到,她把你的大衣搞脏了?”
“没关系。”
“有一次,我把你的大衣弄脏了,你给了我一个耳光。”艾尔莎抱怨说。
“这不是真的。”
“千真万确。”
黛黛在审问:
“为什么她只穿了汗衫和尿布?”
“这样穿就可以了。”
“发生了什么事儿?”
“没什么。现在我们去莉娜阿姨家吃饭。”
听到这个消息,她们像往常一样振奋,上了车。伊玛咿咿呀呀地对两个姐姐说话,她很高兴能得到关注。两个姐姐都争着抢着要抱她,我让她们一起抱着,不要把她拽来拽去的。我喊道:“她不是橡皮!”艾尔莎对于这个方案不满意,用方言骂了黛黛一句。我想扇她一个耳光,我通过后视镜看着她,说:“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你说什么?”她没哭,她把伊玛交给黛黛来抱,她说带着小妹妹让她好烦。后来伊玛伸出手要和她玩儿,她很粗暴地推开了,尖叫着说:“伊玛,别这样,好讨厌!你把我的衣服弄脏了。”这让我很心烦。艾尔莎对我说:“妈妈,让她别碰我。”这时候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发出一声尖叫,这让她们都很害怕。我们就这样在紧张的气氛中穿过城市,只有黛黛和艾尔莎时不时的嘀咕会打破沉默。她们想知道,她们的生活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无法挽回的事情。
我无法容忍她们咬耳朵说悄悄话。我再也受不了任何事了:她们的童年,我作为母亲的身份,伊玛的咿咿呀呀。我几个女儿在车上,我脑子不停地回想之前看到的交媾场景,鼻孔依然能嗅到性器的味道,我不断升腾的怒火开始伴随着那些最粗俗的方言冒出来,我感到很撕裂。尼诺操了家里的女佣,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去奔赴他的约会,根本就不管我还有他的女儿。啊,真是一个混蛋!我真是瞎了眼,他就像他的父亲吗?不,这样的比较太过简单。尼诺太聪明了,他非常有文化,他对于交媾的爱好,和一般南方男人和法西斯分子不一样,那不是一种粗鲁的、对男性气概的单纯展示。无论过去和现在,他对我的背叛源于一种更高级的意识。他有一系列很复杂的思想,他知道他的这种做法会让我非常气愤,会把我毁掉,但他还是会那么做。他想:我不会因为那个贱人跟我吵架,就放弃自己的乐趣。他就是这样想的,他一定会觉得我是庸人自扰——在我们当时的环境中,“庸人”是一个经常用到的词汇——我是庸人,一个庸人。我甚至能想到,他很优雅地为自己开脱:“这有什么问题,肉体是脆弱的,我看的所有书上都是这样写的。”这个婊子养的,他会说这样的话。我的怒火开始转化为恐惧。我甚至对着伊玛叫喊,让她闭嘴。到了莉拉的家楼下时,我对尼诺已经恨之入骨了,我从来都没有那么恨过一个人。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