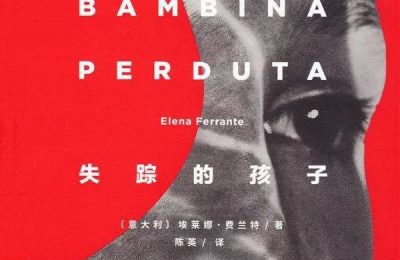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我从我妹妹那里得知当时的情况。她跟我讲这些时,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你们都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但没有我们,你们谁也不是。早上九点整,马尔切洛和一位主治医生一起去了医院,马尔切洛早上亲自去了医生家里,把他接了过来。我们的母亲马上就坐上救护车,被转移到了卡波迪蒙特的诊所里。埃莉莎说,在那里,她受到女王般的待遇,家属和亲戚想什么时候去探望都行,房间里还有一张给爸爸睡的床,他晚上可以住在那里陪妈妈。尤其是,她用一种带有鄙夷的语气说:“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都由我们来承担。”她后来说的话带着很明显的威胁:“也许,你的教授朋友没弄明白他是在和谁打交道,你最好跟他解释一下。你给莉娜那个贱人也说说,尽管她很聪明,但马尔切洛现在变了,已经不再是她当年的那个小男朋友了,他也不像米凯莱,她想怎么摆布都行。马尔切洛说了,如果下次她还像在医院里那样,当着所有人的面那么对他,那就不要怪他不客气了。”
我没对莉拉说这些,我也不想知道,她和我妹妹之间具体有什么矛盾。但在之后的几天里,我对莉拉很关心,我经常打电话给她,想让她知道,我对她很感激,我很爱她,希望她的孩子尽快出生。
“一切都好吧?”我问。
“是的。”
“还是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顺其自然吧。今天你需要帮忙吗?”
“今天不用,明天——假如可能的话。”
那些天好多事儿,新旧的羁绊似乎都叠加在一起了,让人很难承受。我的身体和伊玛小小的身体紧密相连,我没办法和她分开,但我也想念黛黛和艾尔莎,我给彼得罗打电话,他终于把她们送回来了。艾尔莎开始假装很爱这个小妹妹,但她没坚持多久,没过几个小时,她就对伊玛做出很讨厌的表情,对我说:“你把她生得可真丑啊。”黛黛想向我展示,她比我更擅长做一个母亲,有几次差点儿把妹妹掉在地上,在洗澡时差点儿把她淹死。
我需要帮助,尤其是刚开始那几天,我得说,彼得罗自告奋勇想要帮我。他还是我丈夫时,一直都没怎么减轻我的负担,现在我们正式分开了,他不忍心把我一个人扔下,照顾三个孩子,其中一个还刚刚出生。他说,他可以留下来照顾我几天,但我不得不让他走了,并不是我不需要他的帮助,而是他在塔索街上待的那短短的几个小时,尼诺一直在逼迫我,一直在打电话,想知道他是不是走了,想知道他能不能在不遇到彼得罗的情况下,回“他的家”。当然了,我前夫离开之后,尼诺开始忙自己的事儿,他有很多工作,加上政治工作,就这样,剩下我一个人管三个孩子:买东西,把两个女儿送到学校,接她们回来,看几眼书,或者写上几行,我不得不经常把伊玛放到邻居家里。
但这些事情都好办,最难办的是要去诊所看我母亲。我不信任米雷拉,因为两个孩子再加上一个新生儿,对她来说也太多了。我决定带上伊玛和我一起去,我把她包好,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利用黛黛和艾尔莎在学校的几个小时去卡波迪蒙特。
我母亲精神好多了。当然,她还是很脆弱,如果一天没看到几个孩子出现,她就会担心,就会开始哭。除此之外,她只能待在床上,在这之前,尽管很艰难,她还是能走动,她能出去。我感觉,诊所里的高档设施让她很舒心,她得到了阔太太一样的待遇,毫无疑问,这能分散一下她的注意力,让她觉得没那么疼痛。她使用的一些缓解疼痛的药品,会让她忽然很高兴。她喜欢那间宽敞明亮的病房,她觉得床垫非常舒适,她很自豪,因为她的房间里有洗手间,她想起来给我展示一下。“地地道道的洗手间,”她强调说,“而不是一个厕所。”更不用说我把伊玛带给她看,让她很兴奋。当我去看她时,她让我把伊玛放到她跟前,她用小孩的语气说话,非常兴奋。她觉得孩子对着她笑了,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儿。
但是,通常她对孩子的注意力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她会说起自己的童年、少年。她说了自己五岁时的事儿,然后跳到了十二岁、十四岁,她跟我讲了那些年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儿,还有她的小伙伴的故事。有一天早上,她用方言对我说:“从小我就知道人是会死的,我一直都知道,但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事儿会落在我头上,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难以置信。”有一次,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她忽然笑了起来,嘀咕一句:“你没给小孩洗礼,你做得对,这都是很傻的事儿,我现在知道,人死了之后会变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会变成小颗粒。”在那缓慢的几个小时里,我尤其感到我是她最爱的女儿。当我离开时,她拥抱我,就好像她要我像婴儿一样又回到她的肚子里。过去她健康时,和她身体接触让我觉得很讨厌,但现在我很喜欢。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