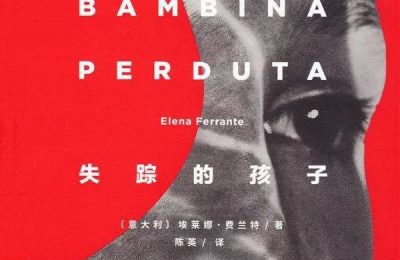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那是非常艰难的时刻。尼诺非常烦躁地回到家里,他很气愤,用方言不停地说:“现在我们看看谁能赢。”我意识到,我母亲住院的这件事情,已经触及到了他的原则问题。我很担心,索拉拉真会把她带到那些为洗钱而设的黑诊所。尼诺用意大利语大声说:“在医院里,你母亲会得到高级专家的治疗,尽管她的病已经到晚期了,但那些教授会让她体面地活着。”
我觉得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越来越关心这个问题了。尽管那时候是吃晚饭的时间,他开始给一些重要人物打电话,都是当时那不勒斯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不知道他是为了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或者说是为了让这些人支持他,战胜不可一世的马尔切洛。但我感觉到,对方一听到索拉拉的名字,对话就变得很复杂,都是那边的人在讲,他在默默地听着。直到晚上十点时,他才停了下来。我非常焦虑,但我尽量不让他看出来,只是不希望他决定再回到医院里去,但我的不安情绪传递到了伊马可拉塔身上。她开始哇哇哭,我给她喂奶,她平静了一会儿,又哭了起来。
晚上我没法合眼,电话在早上六点时又响了,我跑去接电话,我希望电话没有吵醒孩子还有尼诺。那是莉拉的电话,她在医院待了一个晚上。她用非常疲惫的声音,跟我讲了那里的情况。马尔切洛表面上作出了让步,没跟她打招呼就走了。她通过一道道楼梯和走廊,最后找到了我母亲的病房。那里住的全是重症病人,里面还有五个痛苦呻吟、不停叫喊的女人,每个人都很受罪。她看到我母亲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盯着天花板,眼睛瞪得很大,嘴里在念叨着:“圣母啊,让我马上死吧。”她因为疼痛而全身发抖。莉拉弯着身子,待在我母亲旁边,让她平静下来了。现在莉拉不得不离开了,因为天亮了,那些护士都出现了。她打破了医院的规定,这让她挺兴奋的,她总是喜欢干这种事儿。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她是在故作轻松,她为我做了那么多,不想让我有压力。她快要生了,我想象她已经精疲力竭了,她自己本身也有很多事儿。我为她感到担心,不亚于对我母亲的担心。
“你感觉怎么样?”
“很好。”
“你确信?”
“非常确信。”
“你去休息吧。”
“你妹妹和马尔切洛一来我就走。”
“你确信他们会回来?”
“他们不来捣乱就怪了。”
我在讲电话时,尼诺出现了,他睡眼惺忪,在那里听了一会儿之后。他说:
“让我讲几句。”
我没有把电话给他,我说:“她已经挂断了。”尼诺没有抱怨,他只是说,他已经发动了一系列人,想让我母亲得到最好的照顾,他只是想知道他的努力有没有什么结果。现在还没有,我对他说。虽然风很大,天气很冷,我们协商好了,他陪着我和孩子去医院,他会和伊马可拉塔待在汽车里,我在喂奶间隙,去医院里照看我母亲。他说好的,他那么合作,这让我很心软,除了有一件事儿让我很生气,他想到了所有事情,但有一件实际的事情却没有考虑到,他没有记下可以探望病人的时间。我打电话问了一下,然后把孩子包好,我们就一起去了。莉拉没再打电话来,我确信她还在医院里。当我们到医院时,我们发现她没在那里,我母亲也没有在,她已经办好出院手续了。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