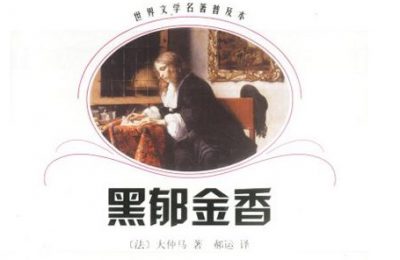《黑郁金香》是大仲马的主要作品之一。小说以17世纪荷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动荡生活为背景。主人公拜尔勒是个完全不过问政治的青年医生。他爱好培植郁金香,并在试着培育一种没有一点杂色的大黑郁金香,因为第一个培育出黑郁金香的人能获得一笔可观的奖金。拜尔勒的邻居博克斯戴尔为了得到这笔奖金,也想培育出黑郁金香。他对拜尔勒很忌妒,生怕拜尔勒捷足先得。他不择手段地监视拜尔勒的行动,暗中破坏他培育起来的郁金香,尔后,他又诬告拜尔勒藏着有损于荷兰总督制的信件,致使他无辜铛入狱,险些被送上断头台。拜尔勒在狱中与看守的女儿萝莎相识并相爱,最后喜结良缘。全书围绕黑郁金香演绎出一幕幕惊心动魄而又催人泪下的场景。
第28章 花之歌
在我们刚刚叙述的那些事发生的那段时间里,被遗忘在洛维斯坦因监狱的牢房里的不幸的望·拜尔勒,正在受格里弗斯给他受的罪。凡是一个成心要做刽子手的看守能够给犯人受的罪,他都受到了。
格里弗斯得不到任何关于萝莎或者雅各卜的消息,他认为这一切都是魔鬼干的好事,而高乃里于斯·望·拜尔勒医生就是魔鬼差到人间来的。
结果一天早上,雅各卜和萝莎失踪以后的第三天早上,他上楼到高乃里于斯的房里去,比平时还要气势汹汹。
高乃里于斯胳膊肘支在窗槛上,双手托着头。多德雷赫特的风车在晨雾茫茫的天边转动。他失神地望着,呼吸着新鲜空气,提起勇气来忍住眼泪,并且保持他那安天知命的心境。
鸽子还在那儿,但是希望破灭了,前途又是那么渺茫。唉!萝莎受到了监视,再也不能来了。她能写信吗?如果她能写,她能不能把信送到他这儿来呢?
不能。昨天,前天,他都看到老格里弗斯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和恶意,老格里弗斯的警惕性决不会放松一会儿。再说,除了禁闭和离别,她不是还有更难忍受的折磨要忍受吗?这个坏蛋,这个无赖,这个醉鬼不会像希腊戏剧里那些做父亲的一样来报复吗?等杜松子酒使他失去理性以后,他那条高乃里于斯接得太好的胳膊不会使出两条胳膊和一根棍子的力气吗?
想到萝莎也许在受虐待,高乃里于斯简直要发疯了。他又感到了自己的无用、无能和渺小。他问自己,上帝把那么多痛苦加在两个无辜的人身上,是否公正。
在这种时候,他的信仰很自然地动摇了。不幸并不能使人增加信仰的力量:望·拜尔勒曾经计划写信给萝莎。但是萝莎在哪儿呢?
他还想抢在格里弗斯前面,写信到海牙去;毫无疑问,格里弗斯一定打算用告发来把新的灾难加在他的去上。但是用什么写呢?格里弗斯把他的纸和笔都拿走了。况且,即使他有纸和笔,他也总不能指望格里弗斯给他送信呀。于是,高乃里于斯把所有这些犯人们用的可怜的办法,都反复地考虑了一遍。
他还想到越狱,这在他天天能和萝莎见面的那一段日子里,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但是他越想越觉得越狱是办不到的。他是那种天性爱挑三拣四的人,讨厌一切庸俗的东西,常常因为不愿走一般人走过的路而失去大好的求生机会。其实那条一般人走的平凡的路,往往是一条四通八达的大道。
“要怎样我才能够从格劳秀斯先生以前逃走的洛维斯坦因逃走呢?”高乃里于斯自言自语地说,“自从那一次越狱以后,不是已经加强了各种防范措施吗?窗户不是已经拦起来了吗?门不是加了两道,甚至三道吗?卫兵不是比以前提高了十倍的警惕吗?
“除了拦起来的窗口和提高警惕的卫兵以外,我不是还有一个万无一失的百眼巨人①吗?不是有一个因为有一双仇恨的眼睛而变得更加危险的百眼巨人格里弗斯吗?
①百眼巨人: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他有一百只眼睛,经常总有五十只睁着。天后赫拉用他来看守变成小母牛的伊娥。
“最后,不是还有一种情况使我失去全部力量吗?我是指萝莎不在这儿。就算我可以花上十年的岁月,做一把锉子锉断我的铁栅,编几根绳子从窗口吊下去,或者在我的肩膀上粘上两个翅膀,让我像代达罗斯②那样飞走……可是我处在一个运气多么坏的时期啊!锉刀会变钝,绳子会断掉,我的翅膀也会在阳光下融化,结果我一定会死得很惨。等人家把我捡起来,我已经摔得缺胳膊少腿,四肢不全了。他们会把我陈列在海牙的博物馆里,陈列在沉默者威廉的血迹斑斑的紧身上衣和从斯塔伏伦③捉来的海象中间。我的计划,结果只会给我在荷兰的博物馆里取得一席地位而已。
②代达罗斯:希腊神话中的技术高明的建筑师。他被克里特岛国王幽禁,在狱中他用羽毛和软腊做成翅膀,飞出去。
③斯塔伏伦:荷兰北部的一个海港。
“可是,不;还是那样好。总有一天,格里弗斯会来害我。自从我失去了快乐,失去了萝莎的陪伴,尤其是自从我失去了我的郁金香,我就失去了耐性。用不着怀疑,迟早总有一天格里弗斯会用损害我的自尊心、我的爱情或者我个人的安全的方式来攻击我。自从我被禁闭以后,我感到有了一股子奇怪的、想找人寻衅的、压制不住的力量。我心里发痒,光想打架,想斗争,我心里有一种不可理解的打人的欲望。我一定会扑到那个老坏蛋的身上,把他掐死!”
高乃里于斯说到最后一句话,咬紧牙关,瞪着眼,停了一会儿。
他心里反复地想着一个向他微笑的念头。
“好!”高乃里于斯继续自言自语,“一旦掐死了格里弗斯,为什么不从他身上把钥匙取出来?为什么不像刚干过一桩最有德行的事似的下楼去呢?为什么不到萝莎房里去找她?为什么不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她,跟她一起从她的窗口跳进瓦尔河?
“当然我游水游得很好,可以带一个人。
“萝莎!可是,我的上帝,格里弗斯是她的父亲呀!不管她多么爱我,她也决不会赞成我掐死她的父亲,虽然他是那么残酷,那么坏。争吵,辩论一定是免不了的,争来争去,副看守长或者那些助手发现格里弗斯还在喘气,或者已经死了,于是赶来,抓住我的肩膀。那时候,我将又要看见布依坦霍夫广场,和那可怕的大刀的闪光,它这一次可不会半途停下来,而要和我的颈背交交朋友了。不能这样办,高乃里于斯,我的朋友,这不是个好办法!
“可是,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找到萝莎呢?”
在萝莎和她父亲不幸的大闹一场分手以后的第三天,我们向读者指出高乃里于斯靠在窗口上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就是这些。
就在这时候,格里弗斯进来了。
他手里拿着大棍子;他的眼睛里闪着邪恶的念头,嘴唇上挂着一丝邪恶的微笑,身子也邪恶地摇晃着。他一言不发,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他的邪恶的打算。
高乃里于斯,正如我们刚看到的,屈服在必要的忍耐之下;这种必要,通过理智可以说已经变成了信念。
高乃里于斯听见他进来,而且猜到是他,不过连头也没有回。
他知道这一次萝莎不会跟着他来。
再没有比对方的冷漠态度更加叫那些正在气头上的人不愉快的了。
一个人花了本钱,总不希望白花。
一个人的脾气发作起来,血也就沸腾起来。如果沸腾的血连一个小小的爆发的机会都找不到,那简直是太不值得了。凡是动坏念头的坏蛋,至少总希望在别人身上老实不客气地弄一道伤口。
所以,格里弗斯看见高乃里于斯一动不动,就找他的岔儿,大声说:
“哼!哼!”
高乃里于斯轻轻地哼着《花之歌》,哀怨但是动人的歌:
我们是秘密之火的女儿,
在大地血脉里流动的火的女儿;
我们是黎明和露珠的女儿,
我们是空气的女儿,
我们是水的女儿;
可是,我们首先是苍天的女儿。
这支歌的温柔的调子,增加了沉静优郁的气氛,使得格里弗斯听了越发生气。
他用棍子敲着石板地叫道:
“哎!唱歌的那位先生,你没听见我在说话吗?”
高乃里于斯回过头来。
“你好,”他说。
随后又开始唱他的歌:
人污辱我们,在爱我们的同时也毁掉了我们。
我们靠一根细线和大地相连。
这根线是我们的根,也就是我们的生命;
可是我们向着苍天举起胳膊,
能举多高就举多高。
“啊!你这该死的巫师!我看,你是存心在跟我开玩笑!”格里弗斯吼道。
高乃里于斯继续唱:
因为苍天是我们的故乡,
真正的故乡,我们的灵魂从那儿来,
我们的灵魂还要回到那儿去,
我们的灵魂,也就是我们的芳香。
格里弗斯走到犯人身旁,说:
“难道你没有看见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叫你屈服,叫你坦白认罪的好办法了吗?”
“你疯了吗,亲爱的格里弗斯先生?”高乃里于斯回过头来问他。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看见看守脸色难看,眼睛炯炯发光,而且嘴上唾沫四溅,就说:
“他妈的!看起来,不仅是疯了,简直是狂了。”
格里弗斯把棍子舞得滴溜溜地转。
可是,望·拜尔勒交叉着胳膊,毫无所动地说:“啊,格里弗斯先生,你好像要吓唬我。”
“嗯!对,我吓唬你!”看守嚷道。
“用什么吓唬我?”
“先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个玩意儿吧。”
“我想这是根棍子,”高乃里于斯平静地说,“还是根大棍子;不过我不相信你是用这个来吓唬我。”
“啊!你不相信!为什么?”
“因为看守打犯人要受到两种责罚;第一种,是洛维斯坦因狱规第九条规定的:
“任何看守、视察或狱卒,动手殴打国家罪犯,一律予以撤职。”
“是动手殴打,”格里弗斯已经气得疯疯癫癫的了,“啊!动棍子殴打,狱规里就没有提到。”
“第二种,”高乃里于斯继续说,“虽然没有订在狱规里,不过在福音书上可以找到,第二种就是: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①
“凡动棍子的,必在棍下丧生。”②”
①这一句见于《圣经》马太福音。。
②这一句是模仿前句造的。
格里弗斯越来越被高乃里于斯的那种平静、郑重的声调激怒了,扬起他的棍子;但是他刚举起来,高乃里于斯就冲过去,从他手里夺下棍子,夹在自己胳膊底下。
格里弗斯气得哇哇叫。
“好啦,好啦,好人儿,”高乃里于斯说,“不要冒丢差事的危险了。”
“啊!巫师,我总有办法治你,”格里弗斯吼道。
“好得很。”
“你看见我手里空着吗?”
“不错,看见了,而且我很高兴。”
“你知道,我平时早上上楼来的时候,手里不是空的。”
“啊!这倒是真的,你平时总是给我送来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坏的汤、最粗劣的饭菜。可是,这对我并不是一种责罚;我只吃面包,越是你认为难吃的面包,格里弗斯,我却越觉得好吃。”
“你越觉得好吃?”
“对。”
“什么理由?”
“哦!理由很简单。”
“你说说看。”
“遵命。我知道你以为把坏面包给我吃就是折磨我。”
“当然,我总不见得用它来讨你这个强盗的好!”
“好吧,你也知道,我是个巫师,我把你的坏面包变成最上等的面包,吃起来滋味比蛋糕还好;这样我就有了双重的快乐,一方面吃起来滋味好,另一方面狠狠地气气你。”
格里弗斯气得叫起来。
“哦!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是巫师了,”他说。
“当然!我是巫师。我不当着众人面前说,因为那会把我像戈弗尔迪①或者于尔班·格朗迪埃②一样送到火刑场去;但是现在只有我们两人,我不妨说说。”
①戈弗尔迪:法国教士,于一六一一年被当作巫师烧死。
②于尔班·格朗迪埃:法国教士,被控把修女送到魔鬼手里,于一六三四年烧死。
“很好,很好,很好,”格里弗斯回答,“不过,如果一个巫师能把黑面包变成白面包,那他要是根本没有面包,不就要饿死了吗?”
“什么!”高乃里于斯说。
“我以后就根本不给你送面包来,看你八天以后怎么样。”
高乃里于斯脸色刷的一下白了。
“而且,”格里弗斯继续说,“从今天就开始。既然你是个那么有本事的巫师,好吧,你就把你房间里的家具变成面包吧;至少我,还可以扣下上级每天发给你作伙食费的十八个铜子放进我的腰包。”
“可是,这简直是谋财害命哩!”高乃里于斯嚷道,一想到这种可怕的死法,自然而然地害怕起来,不知如何是好了。
“好!”格里弗斯继续讥讽他,“好!既然你是巫师,你总可以活下去。”
高乃里于斯又恢复他的愉快的神情,耸耸肩膀说:“你没有看见我从多德雷赫特把鸽子召来么?”
“怎么样了”格里弗斯说。
“怎么样!鸽子烤起来滋味也不错;我看,一个人一天吃一只总不至于饿死吧?”
“火呢?”格里弗斯说。
“火!你知道我跟魔鬼有来往。既然魔鬼离不开火,你以为他会让我缺少火么?”
“一个人不管多么强壮,总不能每天单吃一只鸽子。从前有人打过赌,但是都不得不认输了。”
“当然,”高乃里于斯说,“等我吃鸽子吃厌了,我只消从瓦尔河和马斯河里弄几条鱼上来就得了。”
格里弗斯吓得瞪眼睛。
“我倒挺喜欢吃鱼呢,”高乃里于斯继续说,“你从来不让我吃鱼。好吧!我要利用你饿死我的机会,痛痛快快地吃几顿鱼。”
格里弗斯又气又怕,差点晕过去。
不过,他改变了主意,手伸到口袋里,说:
“好,既然你逼得我不得不来这一着,”他掏出一把刀子,拉开来。
“啊!刀子!”高乃里于斯一边说,一边准备用棍子自卫。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