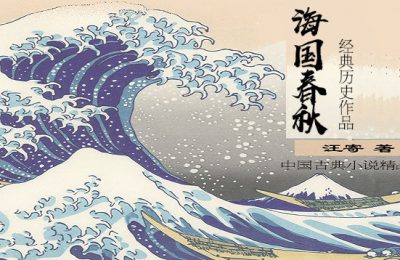海国春秋(原名《希夷梦》)十二卷四十回。作者汪寄,号蜉蝣,新安人。生平不详。乾隆五十一年以前已逝世。据此,盖乾隆时人,书亦著于此时。现存最早的是嘉庆十四年新镌本堂藏板本,又有光绪四年翠筠山房刊本,上海苏报馆校印本,民国年间大达图书供应社排印本。叙述韩速、闾丘仲卿二人在海国建功立业五十年,而两宋兴衰已三百年的故事。清代汪寄著白话长篇神魔小说,《希夷梦》是清代汪寄著白话长篇神魔小说,又名《海国春秋》,四十回,成书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前。此书叙述赵匡胤黄袍加身,举朝归顺。唯韩通全家殉难,李筠起兵讨逆而兵败自杀。韩通弟韩速,李筠幕宾闾丘仲卿,为复仇而投南唐。南唐君臣不思谋国反思媚敌,韩、闾丘离唐往西蜀,途经黄山,被引入希夷老祖洞府。二人安寝石上,乃得一梦,仲卿到海国浮石,韩速到海国浮金,二人各为其主,既立军功又肃吏治。然才过五十年,却遇陆秀夫抱幼主投海,知中原已历三百载,赵氏国亡,元人入主中原。韩、闾丘惊梦,遂从希夷仙去。作品以洋洋50万言讲述一梦幻故事,前所未见,实是作者的一种创造。总之,全书结构、布局比较新颖,故事情节也颇曲折。
《海国春秋》第三十三回
破肚移心善仇都了结 拘魂易体奸恶自灾殃
且说挑夫人众因何发喊争逃?原来潭内老蛟时常率领族类乘风作浪,淹漫田禾,崩堤倒岸,寻觅血食。今日起挑之处恰好与潭间隔无多,蛟怪闻人畜声音,群然腾兴,沙土为所摧毁,水骤涌入、百姓知觉,趋避上高,未曾伤损,驴骡牛马亦俱奔窜。须臾,冲决张大开来,浪如雪山,澎湃盈溢。数十万挑夫袖手观望,牛马驴骡散漫遍野。引笑道:“器用俱失,如何备办得及?”
舒太远道:“且令众内善于工者星夜制造,凡先成者倍给其值。各处民夫并牲口,翻上兴挑。”
武侯道:“前边诸事,二二公任之;潭中蛟患,不佞须熟思之。”
引、舒二大夫遵令,吩咐董事人员逐层传谕下去办理。
武侯乘车复到潭东,令泾邑宰开去海涯边五百丈实土,令蠡口邑宰将老蛟潭掘通,放出海口。邑宰遵令开动,水自归河。突然,下势注倾,奔流逐浪。半天时候,将巨浸之蠡湖泄去大半,仅存东南径约里许半洼碧水。老民告道:“此老蛟窟也权。”
武侯道:“易耳。”
选择后日丙寅开铸,令邑宰采取顶好纯钢,命老民查访近年被蛟害者生辰年月八一十一名。次日齐全,令拣聚坚炭,堆积如丘。又次日清晨,武侯设祭祷毕,起火熔钢,分作八十一份,令老工锻成狮形曲牙钩爪、尾尖锋利倒须刃。每口呼被蛟害者姓名,写生辰于其上,选强弩分列八方,再用蜡绳穿齐,另以铁链沉锋于洼中。始令善泅者着重蜡衣裳巾靴,分布潭内周围,牵拽落底之铁链蜡绳,盘旋扰搅,使刃纵横上下。只见洼底雷鸣沸涌,白浪激昂,众蛟乘之腾空,俱为强弩射落。蜡绳或平排,或交错,往往来来,水俱变赤。受伤之蛟或残形,或半段,纷纷漂浮水面。另用长绳浮木拦入潭边,尽行勾起,大者、小者约数千条:有牛形者,有蛇形者,有独角者,有双角者,有生鳞者,有出毛者,有无鳞无毛而光皮者,有无角者,其类不等。仍令绳刃再四搜取,只见水翻,并无蛟福。武侯思道:“恶类若尽,水不应翻,其中非老蛟则他怪耳。”
忽然忆起元来时闻蛟为害实甚,若不除绝,恐余后患。于是加入牵袖落底铁链绳刃,犹如翻江一般,只见一蛟似龙非龙,周身带伤飞出水面,欲腾空而走,又为强弩射下而死。再看时,水亦不翻,谅蛟已尽,即命泅手上岸。其铸成铁狮即立于岸,又命兵民担土运石,修整被蛟水冲坏之处,其有砂塞者即行挑开。真是为民而不息苦心也。
却说岛主一日对西庶长及广望君道:“臣尝差人探听,闻工虽未尽成,然谅有八九。但此数日未得实信。”
西庶长道:“主上若放心不下,可命西青前去慰劳并探消息。主公以为何如?”
岛主道:“卿言是也。”
于是命西青送解羊酒,以慰劳苦。西青领旨回府。西庶长道:“尔此番前去,一人奉命慰劳,然须留心正务,观其开河之浅深,须详细回报,以免主上挂念也。”
西青领命。次日即起身。
一路饥餐夜宿,十余日已到河边。武侯迎接草篷见礼,坐下问道:“主上可安?遵大人及广望君可好?”
西青道:“皆好。惟主上及老父心中挂念河上耳。”
乃同西青上车,过蠡湖前,西青道:“河由湖傍,湖边有塘,水自不至漫出。其中须待浊水积淤,始可为田,彼时修治未晚。”
行到众工筑挑之所,命河营军土往下流潭边抬回各物。
西青辞道:“奉父亲命前来,各事已悉大略,今谨告归。”
武侯道:“不暇修书,烦代致侯。朝中有独孤大夫、苟大夫、樊大夫与韩子邮,玉砂冈有石大夫,四境关务有杨大夫、水大夫新境有骆大夫、平大夫,河务有引大夫、舒大夫与不佞。请尊公调养贵体,国事毋庸过虑。诸人皆性定不易,惟石仁似乎色厉内荏,恐其心地靡常,仍须体察耳。”
西青称谢,回都去了。
武侯随河审视,凡两边有支河,则将堤凹下一丈,用三和土筑成坚坝,水大则流去,可免漫涨崩岸等患。自枝头邑至天钺山,凡百六十余处,自泾口挑筑至金街坝,凡越二十五月。
将坝掘开,使水尽往下河渲泄,峡内积砂随水泻淌,滚滚滔滔,势如倾斛。然后将上河应剪应浚之处概行挑筑坚实,又于泾口铸铁人、铁兽——不用卧形,俱系行立,向前直指,有奋然奔斗之势。再将金街坝堵断,水始畅流于大河。令往来船只分大、中、小三等,各造铁口粗布袋,沉拖于船边,以取淤泥,四十里一交卸。又凡四十里置堡兵二十名、收泥船十只,收受船交之泥。视堡左右四十里内堤有缺陷处所,便行筑补。
善后事宜一并奏上。
岛主阅毕,使廉勇前来慰劳,并解赏赉赐诸职事人员。武侯同引笑,舒太远谢过恩,款待天使。因见廉勇衣冠平淡,形状猬衰,甚为诧异。廉勇平日奢华艳丽,气宇狰狞,今忽若此,定系亲近正人,变去恶习。引笑忍不住问道:“国舅近来何所际遇,迥非日前规模?”
廉勇闻问,垂泪道:“不幸为妖人所弄,贝山珠藏变为鹤去鱼脱,反背浑身债负。今次讨差前来,望君侯与诸大夫帮助。”
武侯愈加不解,因其垂泪,未便复问。席散,令家丁探其长随,方知就里。原来廉勇因奉廉妃命,到铁围看视辅公,只为举动狂妄,遭人暗谴,致吃大亏。
尔道暗谴之者是谁?乃游石门坞一个奇士。
且说辅公朝夕常在西园接待隐逸,恭敬不衰,凡岩穴湖海之士,往往来来,各无畛界。这日偶到半山阁后,见苟轩案前有位满头白发的老翁,枕椅背而卧,其形甚陋,身旁竖着支紫竹根的拐杖。似乎亦曾会过。问待客各官,无知其来处姓名者,惟云在此坐卧,足不出户,已系半月。辅公猛省道:“昔于鹰巢岭见与大木先生倚柱立谈者,正系此人。形迹古怪,定系小木先生。”
乃拱立于案旁多时,老者醒后,也不起身,伸腰擦眼道:“公无劳苦,老汉午睡未足。”
辅公道:“此非先生卧所,高榻备于正室久矣。”
老者也不回答,依旧睡去,辅公端立以待。须臾醒来,起身笑道:“公误矣,尽礼于老汉何为?”
辅公道:“昱接诸位老先生,教无不用其诚,然称‘尽礼’,则未敢当也。”
老者大笑,携手取杖,转入正室。辅公亲将悬榻放下拂拭,老者道:“公如此,老汉难安矣。请各从其便不必相扰。”
公始别出。问大木道:“老者可系小木先生?”
大木笑而无言,辅公也不复问,率真相待,听其自然。
廉勇奉命到来,恃国舅之势,目空一切。见西园内都系无爵位的贫士,窃怪辅公交接之非。不期小木恰好出游,廉勇到住室内,见窗外景致可观,令从人将所存物件尽行抛出,眺望盘桓。次日,辅公闻知,连忙收拾封锁。廉勇见了不悦,立刻起身回都。去后三日,小木归来,见 物件移易,侍奴告诉情由,小木全不为怪。辅公到室请罪,小木道:“狂童放肆,于公何欤?但伊到此,尚且无忌,平素作为,定然不堪。”
辅公道:“朝中往年余、包,今日余、廉——权倾内外,富敌国家,忠良庶长如西、如顾,俱莫如何,武侯、驸马置之膜视。其党欲危太子,数请立昱,主上、娘娘俱为所惑,赖顾庶长死谏方止。”
小木笑道:“心正,邪奚能人?公无多虑,党事老汉治之。”
辅公称谢。
次日,小木带奚童,携拐杖,离石门西行。半月始到黄云城,赁居于先觉宫。其中供奉的系任圣,香火茂盛,羽客共有三十六房,乃黄云城内外第一个大观院。本来幽静,逢有事故,投寓者多,更觉纷乱。小木赁的华光楼顶,四面轩窗畅爽,不特清静,且高出城头,郊外山川林壑之气象俱可赏玩。
楼下第二层,先有士子居住,诵读之声,旦夕相继,又有啼泣之声若相唱和,殊觉哗喧。这日,偶见东郊古木浓阴,丘阜峻峭,带着奚童携杖往观,方知是邀游胜境。原来黄云城外,岫罗冈前,左山右湖,湖内景致平淡,只产九色莲华,中无间隔。而华依方出色,从未淆混,惟东北系靛边白华,西北系朱边白华。凡蘩苹、藻荇、菱茭等草皆然。左边之山虽系冈陵,不甚巍峻,而丘壑层迭,峦岫蜿蜒,奇难殚述。内中最著名者曰千人石,乃石具古人情状,数足一千,故曰“千人石”。此外,肖鸟、兽、鱼、虫之形者尤多。其东为百谷万卉,乃谷种卉类咸备也;其西为曲水瘦藤,乃水尽曲折之态,藤穷交结之奇也;其南为木丛竹薮,乃竹族俱全,木名悉俱也;其北为幽岩邃谷,乃岩极骇怪、谷沟幻异也。向为行宫禁地,岛主时常幸临。殆包、庄、毕、中伏诛之后,精励政务,命将行宫撤去,人民始得游览。其嘉木美竹、怪石古藤、奇花异草、迭阁盘楼、曲房复室,应接不暇。所尤神妙者,莫如北边之幽岩邃壑。
当日,小木步至林中,意欲尽目之长,穷搜一隅名胜。早见隔溪垒石水纹高畔,数间竹瓦敞篷。行到埠边,涉梁而过,上岸穿篷,沿壁入坞,东南直行到转湾处,无路可走,仰见猛虎蹲踞当途。若非早知系石,却也大为吃惊。旋身四顾,周围罗列峭壁,只有西北瀑水泻响。虬松枝内隐隐似门,行到跟前,却见青石壁间有洞如阙。其旁生就白纹神像鸦状,曰白鸦洞。阶松入阙,曲折而前,望得对过冈上二石似男妇共话之状,曰问答石。行到洞口,却无接脚下踏之处,乃是一片青葱畦圃,曰百草坡。欲仍回旧路,偶见曲折内边东南有隙,便由之直至冈脊,曰通天窍,看问答石形,更觉确切。欲往审视,路忽阻隔,因折西北下冈。冈边有池,水皆黟色,曰洗砚池。
扪山循行,见隔岸数石,如摘取之状,曰彩芝石。池之尽处有岩,曰别有洞天。转南山岩,霖霖水声入耳。其外有石,似持竿之状,曰垂纶石。步近看时,乃藤绕垂,非竿纶也。其下系逶迤石涧,曰飞帛渠,远望两岸,茸茸细草遮满路径。有十数巧石依岸如坐,或正或欹,或俯或仰,曰修禊石。举足欲进,若有所碍,俯而视之,有石半水半岸,曰濯足石。对岸有若坐而曲躬者,曰捣砧石。旋而沿涧行去,隔岸有石耸立,涧内有石似牛,曰饮牛石。先出岩所闻霖霖水声,即饮牛石所激响也。前进壁阻,乃踏角登脊而过对岸,向南转北,望见平坦处曰白云窝,二石并排,曰耦耕石。
及到石旁,为水阻断,涧浒有斜石若船,曰横舟石。上流有长大石,中复有石若坐,日乘槎石。对岸有石若招手,曰唤渡石。转望南边有二石相向:左石上宽下窄,右石上尤宽,如十字,端拱对立,曰举案石。行到石边,有曲径上坡,曰盈芳甸。当坡松下有石曰抚松石。上坡,见松去石尚远。乃自松后而至石前,转往石后,见石上有斜石,曰负薪石。其石旁有石,临涯侧首,日听琴石。左旁有石而首锐阔,曰戴笠石。
涯下有石,胸如臃肿,曰灌园石。去戴笠石数武,冈边有石,若拂袖奔走,曰避人石。上冈有石,迎面仰首若笑,曰浩歌石。望冈岭落处层峦之上,曰炼丹台,有石若端坐,旁有石如炉如灶,曰炼丹石。上至石边,则峦顶有池,形若葫芦,水清无尘,其源自北岭九迭泻下,始至峦顶分贯入池。涧中湍急,而池内无波。
遥望北岭,积翠葱茏可爱,奈无径可往。乃由峦东下,遍地草色如银,曰雪花坪,足忽若虚,锵锵声响,视之,则藤枝漫山,藤叶如雪。叶下黑花红果,名雪中炭。山麓冈旁岩中横石,曰高卧石。去岩十余丈,有石飘然若行,曰寻梅石。随涧转南曰大茗园,山茶未谢,枝旁有石,躬身若浣,曰掬月石。
其山茶色如鹭羽,馥郁扑鼻,干老而枝莹彻若水晶。过掬月石,有斜石散手箕足倚于根株,曰徜徉石。石旁有石,半白半青,曰袒裸石。过袒裸石,依涧稍南,涯边有石,垂肩俯首,曰行吟石。涧水流入石壁,壁阻途断,有藤横空,曰仙子桥。
援藤悬足移过对岸,旋入壁前,度桥入壑为海棠坞,有石上下,分而中合,曰交臂石。进坞石楞树旁,有二石相对弓腰,曰领盖石。坞内海棠为浮石之冠,枝柔叶翠,色淡气馨,名曰沉香。海棠丛边有石,身窄首宽,曰插花石。其旁磊磊,如瓮如瓶。奚童道:“涉溪行曲折十有余里矣,石路高低尖利,赤脚脚底不能堪矣。请暂歇息。”
小木应允,就石而坐。奚童随蹲于后望观对岸。
忽闻呵叱之声,前驱早至。小木起身回避,鞭棒交加。奚童涕泣,小木拖杖拉着,不管路之险易,奔跑向前。奚童脚痛流血,哭号更凶,俱遭打入涧内,混身淋漓。逐驱者扬棒叱道:“还不快走!余大夫至矣。打死汝们无关紧要,我等受谴,寻谁理论?”
小木挟着奚童,拄杖上岸,逾阜穿林,奔出坞外,席地而坐。奚童泣道:“平日言选择,说趋避,今朝游玩千石奇景尚未及百,已受十分足辱。向所言说者,安在哉?”
小木大笑,又见侍从如云拥着个少年显官,乌纱珠履,玉带紫袍,神如秋水,色似梨花。小木暗羡道:“好个清秀品貌,但惜行如摆柳,视若饥鹰,经过之处,香气氤氲,移时方散。询问旁人,方知系当朝第一个幸臣,官拜上大夫,姓余名大忠。小木点头道:“狐媚胜似女儿,莫怪岛主为其所惑。”
须臾,大忠进坞,趋陪赏花的显者络绎不绝。守园园丁将看花游人尽行逐出,园外景致亦复清趣。奚童脱下衣裳,晾于桥栏杆上,小木抚着杨柳,看涧外农民插秧。
忽然皮鞭又自后打来,骂道:“老不死的闲骨头,何处坑里倒不下,偏要横到这里?”
小木笑着走过桥去,回视持鞭的道:“敢过来么?”
那人大怒,欲奔赶来,双脚却似捆在桩上的一般。小木笑道:“少陪了!”
拖着杖子,奚童取下衣裳,缓步而归。奚童问道:“那人要赶,赶不前来,我们走出很远,看他还站在那里哩。”
小木道:“早哩!早哩!”
奚童道:“我们出城时,宫门口哭的那家子,同楼下读书的,此刻都还不曾止哩。”
小木道:“在寓痛哭,定系受人欺累。且听声中有老妇,有少女,老者伤痛,少者忿恨,而俱大恸不休,似有无诉的冤枉。然离西园至此,但见民安物阜,可知政美道隆,乌得犹有冤抑无诉若此之事?”
奚童道:“慢说什么政美民安,我们方才受无辜鞭打,难道有诉处么?”
小木点头道:“尔可前去细细访清,因何啼笑我别有道理。”
奚童去了一个时辰,回来摇头道:“真正奇冤!哭的那人系金鸡郡鸡爪山人氏,母女二人,母约五十余岁,本姓胡氏,嫁与邹家,生得一子一女:女约十五六岁,名唤露珠,子名德盛。德盛原系鸡爪山富产,因与族人争田,恐讼不胜,投在国舅廉勇门下,充当管庄家人。不期砂碛渐加,将田盖漫,尽行荒废。前月廉国舅亲去看庄,见着露珠生得姣好,硬要娶之为妾。胡氏晓得余夫人酷妒——窥见侍妾有与国舅言语的,俱极力责罚,被死者数人——因此不肯。廉国舅便勒令邹德盛赔租,交鸡爪邑比追,将邹家山地、房产俱行抵入,仍不足数。
德盛之妻屈氏气愤而亡,仍然对德盛百般刑法拷问,定要露珠作抵方准结案。无奈胡氏母女二人来黄云城投奔外家,谁知前月搬去岫罗墩,再无熟人。欲回鸡爪,则无家可归,在此权寓而使用又乏。露珠意思寻死,因难丢母亲。前见邹德盛解往鸡爪,形容枯稿,体无完肤。解差不许停留,推折前去,母女急得没法,只有恸哭而已,今已八日了,见者无不辛酸。”
小木道:“无怪声之悲切也。尔明日可买石膏二斤,磨成细末,将楼左边洒扫洁净,取向北木槿干一枝,燃灯三盏,俱置于案桌之下。布宽纵横八尺,待我游戏与汝看。”
奚童欣然。
次日,悉行办就。酉刻,小木焚香燃灯,坐盘案下,密诵至言。用木槿将石膏分开八位,画成山川、烟雾、城郭之形,令奚童也进所布八尺之内,坐于干宫。奚童走入,眼界便宽,似登高峰下瞰城邑。转顾小木,神色庄严,拈着槿枝,于未宫三击。忽然城池出现,阴惨之气逼人。城门划然大开,奔出个白眉曲背老翁,到来参拜道:“本城土地叩首,请祖师真旨。”
小木道:“唤侮魂班幽卒听使。”
土地老翁复入城内领出个判官,随着数十头面各异的鬼卒,齐到坛下叩头,小木道:“免礼。可将本城廉勇、鸡爪邑邹德盛二人躯壳好好取来。”
用木槿于子位上轻敲,门扇豁喇开开。判官领着鬼卒俱入其中,片时扛出个精身汉子,又扛出个戴手铐脚镣的犯人,齐到坛下。
小木令道:“可引二魂出舍。”
判官用手指去,犯人的魂出自鼻中,如蛇行窜,变作人形,仓皇欲走,鬼卒擒住,押跪坛前。
再向精身者指去,寂然无声,二指,三指,亦复如是。判官惊慌跪禀道:“下役法尽,求祖师神通。”
小木道:“邹德盛困苦不堪,其魂欲脱,故指到即出。廉勇恃顽安居,闻风则避,何能轻得?但系财色之徒,为一女子而甘心作恶,须使化邹氏引之。”
判官道:“领真旨。”
命牛头鬼卒变化牛头,用双手将脸搓摩数转,俨然姣好美女,袅袅婷婷,行到廉勇身旁说道:“国舅听禀:而今哥哥邹德盛同母亲情愿送妾服侍国舅,求恩释哥哥!”
道犹未了,只见廉勇鼻中有个猱猴跳出,便左人形,执着美女手道:“尔母亲、哥哥早知如此,也不受苦了,且取乐去来。”
牛头鬼卒用手将美女脸抹下,大声道:“前边是取乐的地方,同尔去来!”
廉魂看见牛头形状,惊惧欲逃,但挣脱不出,战战兢兢,随到坛前跪倒。小木道:“可将二魂气线剪断,互相易于。”
原来,凡魂出窍,俱有先天生成的气线牵连,不能离脱。所以各归各体,从无错乱。当下,判官令鬼卒将二魂气线割断,互易系好。小木道:“且将廉勇之魂入邹德盛体内还原。”
牛头便又向廉魂画上搠,廉魂惊起,奔入邹德盛鼻中,牛头挟着,复入坎地门内。
小木道:“楼下士子劳苦攻读,无有外务,志向堪嘉,可引其魂询问。”
判官领命,亦于坎中领出魂来:周身褴褛,气宇轩俊,约有五十余岁。行到坛前,连打三恭。小木问道:“足下何为而攻苦若此?”
来魂躬身道:“小子姓万名卷,少虽习儒,后以家寒易业。今见《诗》、《书》理义远长,好之忘疲,无所求也。”
小木道:“志何所欲?”
万魂道:“天下人心一般平正,饥者有食,寒者有衣,正偏邪之心,无冻馁之民,于愿足矣。”
小木道:“心地偏邪,自受加倍磨折。汝不必管。廉勇富于积敛,今西南民荒极苦,易汝心而布散之,以遂汝‘民无冻馁之志’如何?”
万魂道:“此不义之财,正合为之分散。”
小木吩咐判官道:“可将二心互易。”
判官令鬼卒往坎门捧出力卷之心,又取廉勇的心呈到上边。小木见形色相似,惊讶问道:“何二心之不殊也?”
判官禀道:“若同而实异:廉勇之心圆而黑如炭,孔窍煤烟堵满;万卷之心圆而青如莲蕊,瓣瓣玲珑。一系仙道将成,一系阿鼻木入。小木道:“闻所未闻,见所仅见。可将万卷之魂藏于心内,入廉勇之腹,以行其志;邹德盛之魂入于廉勇体内,以复其仇,亦使还原;廉勇之心暂安万卷体内。”
判官领命,令鬼卒捧着青心安入廉腹,缝好肚皮;再将邹德盛之魂推入廉体负去。回来,小木吩咐道:“二七后候令。”
判官道:“领真旨。”
吩咐鬼卒守视。三个鬼卒仍入坎宫,土地、判官等俱还本地城内。小木将金钟轻扣,百般光景事件,随声澌灭。
不说楼上事务,再说邹德盛原系廉勇,发回鸡爪邑比追积欠,收在禁中,乏钞使用,无苦不吃,仅存微喘,仍拘压于柙床之内,廉魂易体,哪里得知?只道仍归旧舍。躲脱了牛头,又不敢撢动出声,及至闻得鼻鼾习习,秽气腾腾,好生惊疑。
欲将身子转侧,始知挤靠得紧,而且九窍百骸旧痛带引更甚。
大喊道:“苦杀我也!夫人、侍婢在哪里?”
连呼数声,将狱中众卒惊醒,恼怒道:“这个穷根死囚!众爷们受尔的累少么?
爷们好好的睡着,还要大惊小怪,喊醒陪尔!想系身子不快,要人服侍么?”
众卒来将柙盖独开提出,将遍身黏在床内的脓血痂子尽行撕下。廉魂痛入骨髓,大叫一声,昏死过去。狱卒掷于地下,用热尿灌醒过来,满口臊臭,心翻欲吐。狱卒见已醒回,用脚拨来滚去,使无皮肌肤碰着尖利砖石砂子,陷入肉中,痛攒心肺。廉勇只道仍系鬼卒,乃哀告道:“诸位神祗,弟子作恶多端,但求放还阳世,情愿改过自新,延请道德法祖荐拔诸位早升仙界。”
众狱卒道:“好!好!先还将爷们作人,此刻将爷们当鬼骂哩!还不打么?”
当用麻辫捆起,使竹枝、皮条安排击敲,下面复上,翻身旋转,无处不到。任他百般告苦,万种哀求,总付之不理。及至血流遍地,痛极死去,方才住手。又用尿灌醒,捺入柙床。廉魂骨节处处胀裂,哼呻无力,看看渐渐天亮,虽系狱中,而声音俱系人象,终不解缘由。大小便溺俱任自然。饿得喉内生烟,腻虫啮腹,每日或一餐半顿,或无粒米滴浆。
如此到第五日上,都中文到,提取起解。众狱卒用药水细洒,将疡痂浸软,离而不黏,扶出柙床,寻饭喂道:“邹德盛,恭喜你从今不受苦了。这般冤屈,人人皆知。我们都系奉命差遣,当知对头系国舅廉勇,为着令妹,必欲置你于死地。此去白杨坞、秋声谷、鬼门洞、汇池关、杳薪壑等处,都系结果、超生之所,须要自家明白,寻廉国舅那厮报仇索命,不必记挂我们。”
廉魂饿得凶,将半钵酸饭吞完,狱卒犹未说了。乃问道:“蒙情谆谕,不解情由,告借镜子一用。”
狱卒道:“牢里那有镜子?尿缸内混混罢!”
廉魂寸步挨到缸边,照着大惊道:“缘何将我变做邹德盛。”
狱卒笑道:“系邹德盛变做死囚,非尔变邹德盛。”
廉魂道:“而今可到得都中?”
狱卒道:“莫想!
莫想!凡提去的囚犯,半路上九个要送死十个,今次的朋友,系旧相识,他们行径不瞒我等。据看起来,大约在白杨坞就要送尔归天哩。”
廉魂道:“我非邹德盛,实系国舅廉勇,因遭妖人作弄,将我变改受苦。”
狱卒道:“这些闲谈,无论真假都不必说。尔只记定冤家不系我们就罢了。尔若系邹德盛,只须寻廉勇报仇泄恨;尔若真系廉勇,只算自作自受,还须自怨,何必害人自害到这地位,其余的话说也无用。”
廉魂急得无法,只有痛哭,随众卒出狱。
邑宰点交提差,带上大路。提差道:“朋友脚下放紧些!我们奉廉府钧命,立有限状。尔的疼痛无关紧要,误了日期,不是当耍的。”
廉魂道:“爷爷,囚犯非敢怠慢,奈这铁镣贴着伤痕,黏动痛彻心肝,如何快得来!”
旁边帮差便将棒照脊梁扫来,骂道:“我们叫尔,是不听的;须他叫尔,方才肯依。”
廉魂痛得跌倒在地。帮差道:“睡下就算罢么?只要尔安稳!”
举捧乱打。看看不动了,已经死去,方才停住。片刻苏醒,提差见实实伤重,乃顾竹篮盛之而行。沿路颠簸,脓血淋漓,皮肉受苦,较朴击更甚。却得余茶剩饭,不致十分饥渴,数日已到都中。
再说邹德盛魂入廉勇体内,半夜醒来,觉得浑身松爽,兰麝扑鼻,被褥温软,身旁睡着肤滑如脂的妇人,不禁情兴勃勃。妇人已醒,便挨来搂定,怀抱上身。邹魂久旷,那顾好歹,便鼓勇驰骤,妇人竭力殷懃。约有一个时辰,花颓柳困,二个时辰,勉强撑持,降书数递矣。邹魂畅极,始罢战收兵。
相猥相倚,睡到五更,宅门传点,请速上朝。邹魂茫然,妇人道:“往时国舅最早,今日之迟,想由于欢娱所致。此刻已系时候,不可再缓了。”
邹魂起来,出得房门,便系万魂主张,各事明白。先令往鸡爪邑提邹德盛,再冠带上朝。朝毕,岛主道:“今据西边郡邑奏称,峡内连年水荒,盖藏久罄,丁壮流离,所存女妇老幼,必致尽填沟壑。请开仓发赈,以安民众。国舅西边庄子颇多,定知情形真假。”
万魂奏道:“臣仓卒记忆不起,容臣回家查明覆奏。但国帑存贮未充,连年砂税虽足,而河工所耗不少;苑围虽减,而赈济用费颇多。此事如有所需,臣愿独力输家助国。”
余大忠慌奏道:“此案工程,非千百万不能办。国勇急公,出言甚易,事或莫敷,岂非欺罔!”
万魂道:“所言甚善。大夫素受天恩,渥极厚至,如勇欠缺,亦应以家之所有尽输佐国。”
独孤信天、水湖、樊勇、蒋义等齐声道:“国舅之言是也。余大夫之意若何?”
大忠急得没法,只得随口道:“敢不竭产以报大恩!”
岛主大喜,诸人随亦退朝。
万魂到家,查点家资,开册进呈。当下,四大总管禀道:“资产乃多年机计所得,成就甚非容易,奈何任兴倾家?”
万魂大怒道:“这些家产,不知刻剥多少穷民,受若干嘴怨,尔等狐假虎威,趁火打劫,于中取利。我今散之以避天谴,以释人怒。尔等犹来假忠假勤,可恶极矣!传外班,每人重责八十,资产查籍,添补佐助,全家发往落鹏山后开垦。”
不容分诉,杖毕,立刻查籍发遣。四人平素作恶染指,今朝何在?当下,再唤掌管将家中所有估变作价。掌管道:“西边峡内九郡七十二邑,按烟户册上贫户,老幼共八十余万口,应二千六百余万贝,方够办公。今府内新老各库共四百万贝,田产各物变易照时价值九折,可得八百万贝,只敷一半。”
万魂道:“家中还有哩。”
掌管道:“东边各库,乃舅老爷余温侯寄存的,共一千万贝。”
万魂道:“可以借用。”
掌管道:“也还不敷。”
万魂道:“再可于他处加息借贷,凑足济用。”
掌管遵命下去,呈上四百万券文请押。万魂押毕,掌管执往外去。半日如数将贝辇归交,易田产物货,日半俱毕。万魂大喜,即命运到玉印郡中,令各郡搬去散给。掌管道:“如此迟矣。各郡邑俱有办事人在都中,可呼来交彼等,择便路而运,不必多玉印一转也。”
万魂依允。掌管往外传各郡邑坐都人,具结领去,两日俱清。
余大忠闻知,急忙来见妹子。余氏因连夜劳倦昼寝,推病道:“有话请与国舅说。”
余大忠问廉勇道:“妹丈何事丧心病狂?”
万魂道:“向来为尊舅所误,使我为守财奴。今日如醉方醒,如梦初觉,自悔当日惟利是贪,不顾仁义。今将所得非义之财共散与贫民,以消当日之罪也。尊舅亦要改换初心,广行仁义,千万不可怀奸而贪细民之利,以受天之谴责也。”
大忠怒道:“尔自丧心病狂,而反道人之黑白也。”
言罢起身回府而去。
万魂含笑入房,对夫人道:“尔兄到此,我将正言劝他,反大怒而去。”
夫人笑道:“他是当日之心,老爷是今日之心,故所言难合也。”
万魂笑道:“夫人之言是也。”
又问道:“此时日已将午,为何还不起来?莫非身体欠安否?”
余氏笑道:“并无别病,因尔昨夜颠狂过甚,一夜未睡,今特昼寝以补昨夕之倦耳。”
说了,含笑即起身下床。万魂举目一看,见夫人身红衣花履,面如带雨桃花,一时兴动,即将左手搭于背上,右手解衣,就床边椅上云雨起来。有两个时辰,方得雨散云收,扣衣出房。便呼掌管道:“尔可查看还有多少贝?”
掌管道:“片贝皆无,尚欠借项五百万贝。”
万魂喜道:“今日方称我心也。”
于是饭毕回房安寝,又同余氏癫狂半夜,直至五更方止。原来万魂是一个少年童身,家又从未见过女色,今见余氏天姿国色,如何不爱?真是“久早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实无穷之乐也。
却说廉勇的魂入邹尸而醒,即大喊道:“快拿茶来!”
禁子大怒道:“尔敢大呼大叫,想是讨死么?”
廉勇闻言,仔细一看,问道:“此是何处?”
禁子道:“难道尔在做梦,连地方都不认得了?”
廉魂道:“我真作梦,到底是何地方,即望教我!”
禁子道:“此牢监也,尔真作梦不成?”
廉魂大哭道:“我为何牢狱之中来了?我夫人怎么不见?”
禁子道:“听尔之言,真是借尸而生者,但口叫‘夫人’,尔到底是何等样人?”
廉魂道:“我乃国舅廉勇也。”
禁子道:“尔这死囚,敢称国舅,真是自己讨死了。尔若再哭,我便打死尔。假如尔真是廉国舅,也是尔平日恶贯满盈,天理自然昭彰也。”
廉魂一听,更加大声哭起来了。禁子见如此,遂大怒,便用皮鞭打有百十余下,打得遍身皮破肉烂,鲜血淋流如雨。
不提廉魂在狱受罪,且说木道一日将万魂召去,万卷便死在床上。道人及寓客闻之,忙至万卷寝室,见尸卧榻上,虽无呼吸,但面容未改。正疑惑之际,有人揭衾,视之,众皆大骇,竟胸剖无心矣。
其时,小木闻知,怪道:“胸如何剖而不收也?”
走下楼,入房中看,用手抚道:“浑身犹温,羽士可遵守,七日之内当回,否则,二七必回矣。此刻惊慌,恐致误事。”
旁人问道:“此系何症?”
小木道:“此名易心,非病症也。——将恶心来易去善心,以行善事,不久自还原耳。”
众人将信将疑。羽士着道童看守,小木回楼。
到十四日晚间,仍如前布置。三处鬼卒同判官、土神齐现,小木令判宫率鬼卒复将廉、邹二身抬到,将两魂气线解开,互相还原,又将二心易转。
再说廉勇本魂回壳,就像浑身仍系痛楚,口中不住的“啊哟哟”。余氏想道:“定因连日房事太劳,叫侍妾取参蓍汤,廉勇方才明白系自己家中,始痛哭起来。”
余氏惊问,廉勇将受苦的话详尽告诉。余氏将上朝倾家赈济的话诘询,廉勇大惊。
余氏道:“可知那人姓甚名谁,家住何处?”
廉勇道:“我哪里问他?”
余氏道:“家私俱被散尽,仍驼债在身,不追出这个人,怎样得了?”
廉勇道:“我若追他,倘又将我换去受苦,如何是好?”
余氏:“尔这样孬!我和哥哥说去,托他缉访。”
廉勇哭倦睡去。
余氏好生懊恼,坐待天亮起来,并不拭拂,乘车归余府。
家人到朝房报知,大忠随即回家。见余氏这般形状,问道:“好姝子有何事故,恁的早起?”
余氏将廉勇的话细说清,嘱大忠定要追人还他。大忠道:“顷在朝房,闻说日前先觉宫失心的寓客今朝复活了。如此想来,妹夫昨晚还魂,可见布散资产即是寓客所为。只须拿住此人,便知端的。”
余氏道:“费哥哥心,嘱役好好唤至,切莫难为。先送来看,待我审问他。”
大忠令家人持信符,同司城大夫一飞往擒拿。家人得令,持符到司城衙门来。大夫吉存见了,立刻带领人役办备物件,上马到先觉宫,径往楼下,见门已锁,慌问道人,答道:“这客醒来,说此地有鬼怪,捆背行李,辞房移去。”
吉存问道:“他往哪条路?”
答道:“不知。”
吉存大怒,令押着道人并近寓众客做眼,分途急迫。人役上楼搜寻,见小木正倚栏远眺,不管好歹,拖拥下楼。余府家人认得小木,慌向吉存道:“此系妖人。”
吉存道:“如何晓得?”
家人道:“数日前,他闯入海棠坞看沉檀海棠,硬不回避余大夫,被驱逐出门外,仍用杖回指我,不但不能动脚,连手也垂不下来,直站到第二日方得移行。妖法何至如此!”
吉存叱令锁拿,众人将带的猪、狗杂血,向小木头面浑身倾泼。小木也不推辞,随他拿进余府。廉夫人看见形状,听了声音,回道:“不是,不是。”
大忠道:“且置监,候我事定,另行研讯。”
吉存遵命,送小木入狱,严加拘禁。
尔道大忠有何事未定?乃因许成仁等在新境贪婪不法,俱被辅公查访明白,据实参奏,请于铁围正法,并命平无累分头擒拿,委员接任。岛主阅过本章,付余大忠看。大忠始知明参四人,暗实指他。因心生急计,奏道:“伊等索受天恩,至渥至厚,平日矢口捐躯报国,大忠深信之。不意到任狂悖至此。
请命提到都城,待臣严讯,他们当日所言安在期!”
岛主依允,立差侍卫田庄、信可复往铁围提取各犯。大忠又似定口供,差心腹家人沿途迎去,密令四人照样依允。因有此心事,所以将小木置监再讯。
小木在内坐了三天不见动静,乃诵至言,狱神出位参见,下面仍有许多苦魂叩头号诉,俱系大忠等陷害死的。小木役狱神往余家探视,狱神带领余家土地来言:“余大忠嘱妹子廉夫人入宫说廉妃道:‘许成仁等并无实迹,因与骆焘、西青不睦,故二人文致其罪。但许成仁等俱系驸马荐,今若加罪,须连坐驸马。请娘娘斡旋。’岛主因廉妃进旨,有不治诸犯之意。”
小木笑道:“此等阴谋,谁人得知?这还了得!该神可将余大忠的魂灵拘来。”
狱神道:“余大忠顽福犹有三十年未终,现有吉星庇护,小神职卑,无济于事。”
小木道:“易耳,将手来!”
狱神双手迎上,小木于左手上写“拿余大忠魂灵”六字,狱神同土地前去,片刻拘来。余魂倔强不服。众冤鬼争上索命,凌辱齐加。余魂始惧,奔跪小木身旁,叩求保护。小木道:“易耳!”
乃唤马面负之,日夜循行浮山。凡遇四生六道身体受苦,将此魂推入代受,每天更换一处。马面叩头领命负去。乃与众怨鬼道:“大忠赏尽乐事,作恶多端,但其阳寿未终,今使其魂生受万种苦楚。待数尽之日,汝等报复未晚。”
众鬼叩谢而散。
再说余大忠生魂已失,次日早起忽如痴迷,岛主传召也不知起身。家人因使命催促,只得扶上温车入朝。岛主往日与他说话,俱系随即回答,今朝连询数事,无半字奏复。岛主大惊,追问,方知系早晨新得病症,叹息不已。因命廉勇道:“国舅系大忠至亲,可送归家,延名医诊治。”
廉勇领命,同车到余府,延安太医诊道:“此为失魂之症。乃灵性误离神舍,归来自愈,可勿药也。”
廉勇同大忠之妻、子,皆知安太医系国手,今如此说法,只得随他。
数日,新境诸犯皆已提到,岛主欲行释放。樊勇奏道:“诸贼臣坏祖宗法度,愿主上急付有司诛戮,以存国体。”
岛主素知樊勇忠贞,拂他不过,因命付司寇置狱,待大忠病愈,令其严讯定夺。乃将诸犯入监。许成仁寄信托廉勇料理狱事,奈手内无货,空口白说。各处反将暗苦与他们吃,都使人来切怪。廉勇无计可施,先所借贷之货,又俱追索,大忠妻子取讨不休。余氏只想着前日床席的人,懒怠贪眠。廉勇无法,只得令亲信仆妇入宫向廉妃诉苦,求命出差,索些酬赠以完债利,所以奉命赉赏来到天钺山。见武侯问及,便求帮助。
武侯使长随探访廉勇家人,只知得了狂病,将家私尽行挥散,不足,犹借重债,尽情凑用,病好,悔已无及。却不知由于小木换心易体的缘由。当下,武侯大笑道:“原来如此!前日虽闻国舅捐资发赈。只道系借公为名,侵渔饱橐,那知实系他的家私。而今倒苦了!”
次日,拜候廉勇道:“闻得为国输家,可敬!可敬!”
廉勇叹道:“莫说‘敬’了,各债追索得凶,求君侯帮助!”
武侯道:“仅以不佞两月俸禄奉赠,诸大夫苦而且贫,国舅无庸措意。”
廉勇虽嫌轻微,然见武侯刳出己资,不便再请,只得谢别回都。
武侯仍于天钺山起程进峡,沿途观看风土所宜,教以树艺。湾中淤积砂砾,俱随便设法疏去。五个月后始到龙楼冈。
引、舒二大夫禀道:“今全河复古,卑职二人附于骥尾,光辉史册,平生愿足。窃爱龙楼内外山幽水奇,敢辞君侯,徜徉于彼。”
武侯道:“不可。治河俱二大夫勋劳,回朝自有上赏,何以隐为?”
二大夫道:“除君侯,无人知用某等者;某等除君侯,亦更无才德可服心而甘为之用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而不知退,待不得退时,思退而追悔,不亦晚乎?”
武侯称善。二大夫长揖登舟而去。
武侯嗟叹,望不见船,始看水势汹涌迅急,逊于往时。行到冈北,见涡漩不减前岁,想道:“曾命车夫在此间守看形状,今不知存亡。”
四处观望,见树桠上架着车子,武侯道:“车在此间,人必未去。”
正在这里叹息,忽闻啸声出自树杪,响彻霄汉。入林视之,闻呼道:“老客好大胆!不怕猩猩么?”
武侯听得系车夫的声音,惟加清越耳,却看不着人。因亦呼道:“猩猩好坏眼睛,连故交都忘记了!”
又闻道:“老客不惧,吾自来也。”
忽闻枝叶萧萧淅淅,已到面前:浑身毛羽莹彻光彩,骨肉皆如玻璃,无有间隔。武侯惊道:“缘何得以至此?”
毛人道:“自老客去后粮尽,而所见未实。思去,则恐无以赞助为民之志,因困于此。欲为厉鬼以除害,偶来有女子,见我甚惫;于篮中出物以餐,并传辟谷之草实,因此得生。如法寻彩,五月正成此形,至今饥寒不识矣。”
武侯道:“足下大道已成,皆由于为民除害之念切。请问所见的实情形若何?”
毛人道:“凡水内众怪欲出之,先地气熏蒸,如将瀑雨,其漩涡渐平,忽又大陷,后再涌溢,水如墙立,向上奔去,底露空洞。
先系赤发青身者数十,争出踏水而行,随后如龙如蛇,如虎如牛,百种状类,不知其数,奔乱窜,河中滴水俱无。约半天时候,水渐流回,各怪随至,牛马驴骡俱被擒获。有一怪捧一件者,有数怪分一件者,成群结队,跳跃旋归,水始聚冲而来,复成漩涡矣。”
武侯道:“此易治矣。檄饬龙楼郡大夫龚吉,令龙楼冈以上五十里,两岸众百姓各备强弩,逢蒸热之时即令探视。如果怪出水涸,密布两岸,以守其归。用橄榄汁渍浸矢镞,认定射之。杀一怪者,以军功一级论。”
发檄之后,别了毛人仍往上行看,直到四辅山。沿途访问百姓近患若何,俱云今岁未曾伤人,牛马等畜亦多获免。即往年水溢不过二三次,今则每月二三次矣。武侯道:“似此,民业益难安矣。须尽除之,地方始得宁静。”
乃登四辅之巅观望,落鹏山秀峰排列,隐隐接天。叹息道:“今如前往登览,又为引、舒所非也。”
回车,不止一日到龙楼冈,龚吉接道:“自君侯进山后五日,水溢怪出。如命伏弩以乘其归,水族着弩,无不倒地。及射后来赤发青身各怪,矢莫能入,安然而行。见各族类受伤,又代拔去弩矢,取泥敷疮,倒者皆起奔归,并未获住一个。”
武侯惊道:“似比,则难治矣。当熟思良法以除之之。”
再寻毛人,已无踪迹。郡大夫于林中竖起帐篷,武侯进内便卧。
约过半日,跃然而起道:“有法可用矣。”
令郡大夫铸造备办诸般物料药材,并行天汉川取白猫竹,行流砂河取金针鱼候用。郡大夫遵令,分头飞饬。正是:水族成精凶可恨,贤才设法智非常。
欲知如何除此伏流内水怪之法,且听下分回解。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