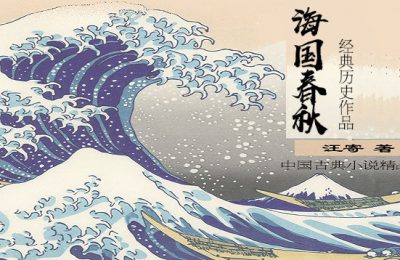海国春秋(原名《希夷梦》)十二卷四十回。作者汪寄,号蜉蝣,新安人。生平不详。乾隆五十一年以前已逝世。据此,盖乾隆时人,书亦著于此时。现存最早的是嘉庆十四年新镌本堂藏板本,又有光绪四年翠筠山房刊本,上海苏报馆校印本,民国年间大达图书供应社排印本。叙述韩速、闾丘仲卿二人在海国建功立业五十年,而两宋兴衰已三百年的故事。清代汪寄著白话长篇神魔小说,《希夷梦》是清代汪寄著白话长篇神魔小说,又名《海国春秋》,四十回,成书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前。此书叙述赵匡胤黄袍加身,举朝归顺。唯韩通全家殉难,李筠起兵讨逆而兵败自杀。韩通弟韩速,李筠幕宾闾丘仲卿,为复仇而投南唐。南唐君臣不思谋国反思媚敌,韩、闾丘离唐往西蜀,途经黄山,被引入希夷老祖洞府。二人安寝石上,乃得一梦,仲卿到海国浮石,韩速到海国浮金,二人各为其主,既立军功又肃吏治。然才过五十年,却遇陆秀夫抱幼主投海,知中原已历三百载,赵氏国亡,元人入主中原。韩、闾丘惊梦,遂从希夷仙去。作品以洋洋50万言讲述一梦幻故事,前所未见,实是作者的一种创造。总之,全书结构、布局比较新颖,故事情节也颇曲折。
《海国春秋》第十二回
寻良友雾漫认龙驹 夺佳人阵前成败犬
别的放下不提,且说子邮在黟山洞天温石床上,同仲卿抵足而眠,乍闻响动,心惊醒来,东方已亮。坐起看时,不见仲卿,连呼无应,床寻觅,并无形影,想道:“仲兄抱负奇才,必因同行多所不便,故乘我睡熟而暗去耳。”
搭包仍在,惊道:“难道到前途行乞么?况入蜀尚有数千余里途程,山泽多蛇虫虎豹,设若犯着,岂不送了性命!我复国时何处寻帮手?必须赶上同行,方免失误。”
乃将搭包带了赶奔。降危梯,登高槛,转弯下到洞前。微雾渐起,想道:“真怪,此断绝路途,仲兄体质柔弱,难道盘过去了?”
乃跃跨松树,双手持藤,交换直上十有余丈,不期惟急,用力太猛,将藤拉断,坠落下来。涧中雾气甚浓,审视不清,深浅莫测。慌忙放了藤,涌身跳跃,奈系峭壁,虽可借势,莫能停脚。跳不得上,只有往下,渐次到底,审视全无路径。
忽闻水响异常,向前望去,依稀是匹赤兔马在涧中滚澡,喜道:“马既能来,人自可去。”
便超身跨上,那马着惊,往前奔腾。子邮用两腿夹紧肋腹,再抓鬃鬣,却是满颈鳞甲,并非皮毛,猛然吃惊。那马不住地跑,却未闻啼声,或东或西,或升或降,皆在雾中。要下又不敢下,只得听其自然。
约有个把时辰,只见雾气渐谈,一轮太阳当空出于雾上。定睛看时,却系跨在赤鲤脊上,大惊想道:“我说如何无有鬃毛,原来非马。今游于雾中,正是游于水内,比汴梁湖中更险,茫荡浮乏,无有涯际。昨日仲兄为猿所引,我今日又为鲤所诱,引到山中,犹有生途。如何作法?”
心中正无主意,太阳忽又隐入深云,赤鲤也渐低落,朦胧看,俱系云波巨涛,不见畔岸。急得无法,只有两手将鱼头兜起。那鲤奋冲,怎奈重雾重重。再行兜起,又往上飞。如此数次,隐隐见下面有凸凹不动之形,大约是实地了,始随鱼落,渐渐看得亲切,是山川人境。又恐鱼不归于此,乃用力压坐,霎时到地,却系潭边。正欲下来,那鱼打滚,便蹿入水。
子邮就地坐着,定定神思,立起身来,缘潭边岸,寻到大路。见往来者衣冠,殊非时制,不知系何处地方。行人亦答以拱,但所回言语,皆不明白。且问且行,音容无二,好生疑惑。
后见老者抱着婴孩,坐在车篷上,看牛医医牛,复恭询之。老者起身答礼,回言亦不能识。子邮用指头于车凳上写,老者点头,走去家中,取只瓢向溪中舀水,就地取土投入搅匀,令饮。子邮见老者气象温和,料无凶意,看老者比划的意思是:“吃得土水,就明白了。”
子邮照办,果然有效。老者道:“足下想是外国人,乘风到此。”
子邮道:“乘鱼。”
老者道:“今早好大雾,可是乘雾?”
子邮道:“正是,老者何以知之?”
老者道:“曾闻鼍龙蟒蛇鲤鱼,皆可乘雾而游。今闻乘鱼,或者人乘鱼,而鱼乘雾耳。”
子邮道:“此处常有人乘鱼么?”
老者道:“小老痴长七十岁,未曾见过。”
子邮道:“所乘之鱼,跃入前面深潭中去了。”
老者道:“前面乃是火龙潭,曾闻老辈人说,内有火龙潜修,未闻内有飞鲤。”
子邮问道:“前何以知有火龙潜修?”
老者道:“离此西南二千二百里,有不夜湖,相传内有神蚌,不知年代,珠巨如斗。群蚌之殊如龙眼、如弹丸、如湖桃、如梨,大小不等,夜则群珠吐光,长年如昼,所以名为不夜湖。火龙贪神蚌大珠,数行强取,一日为神蚌将爪夹断,不能上天,只在潭内修养,所以唤作火龙潭。”
子邮道:“贵处属何州县管辖?”
老者道:“什么州县?”
子邮道:“凡天下人民居住,有地名,自有州县各官管辖。”
老者道:“敝处系火龙邑,为浮金之边境,邑中有宰。此地名单家瞳,不知何为州县。”
子邮道:“可晓得汴梁离此处若干路?”
老者道:“何处唤做汴梁,属何邑管辖?”
子邮想道:“这老儿连汴梁都不知,与他说什么!”
拱手欲别,老者扯住道:“你系何国人氏?”
子邮道:“中华人氏?”
老者道:“中华可是刘季家中华?”
子邮道:“哪个刘季?”
老者道:“诛秦灭楚的刘邦。”
子邮道:“正是。”
老者道:“老汉姓单名义,字行宜,先祖于隋末自中华飘来。足下尊姓尊字?”
子邮道:“不妄姓韩名速,字子邮。”
老者道:“中华来的,都系家乡人了,可到小庄歇息。”
子邮心中总不明白,亦欲细问,始随单义到庄上来。单义笑道:“昨日得有野味,应以敬客。”
引子邮入旁垣中。只见天井内有堆灰火,三人在旁坐着,见进垣,俱起身迎。单义问道:“好吗?”
回道:“好矣。”
单义道:“可将野味取来。”
三人将火拨开,抬出个大泥团,将泥扑去,却系个大瓜,馨香美味从中溢出。抬到阶前,复将小瓮置灰火中,将瓜盖掀开,用叉逐件取出,却系一个虎头,四个虎掌,四只虎腿,数块虎筋,一条虎尾。单义请席地坐下,举叉将虎头尾敬到子邮面前;又将灰火内小瓮取来,置于瓜旁,揭去土盖,乃系盈瓮酒酿。单义举勺,先请子邮三勺,后白饮二勺,下三人各二勺。单义取掌,三人各取掌。子邮用叉食头,味虽甘脆,却带酸腥。连尾吃尽,诸人掌方食毕。单义复将筋俱敬来,子邮也不推辞,举叉又食,举勺饮酿。四人连腿俱吃不下,子邮将筋都食尽了,众人吃惊。子邮问道:“此味究系虎,系鱼?”
单义道:“系鱼系虎,乃虎化鱼未成,名为虎鱼,若化虎出水,平阳无不受其虚害。凡食之者,风疾俱愈。其皮可为甲,刀箭难入,常油漆之,渡水不沉,十分贵重。”
子邮谢过欲行,单义道:“今日幸遇,足下到此又无亲戚,何不在小庄盘桓数天,略知此地风土人情,往前行去,也免出笑话。”
子邮想道:“其言近理。”
依从住下。单义复问些三代古迹,子邮随事答应。天晚送上酒来,又问些中华诸酒之事,很晚才住,四人醉了。单义送子邮进庄歇宿,拱手别去。
子邮和衣就枕,一觉醒来,辗转再睡不着。下床行到垣中,徘徊多时,欲复上床,忽然垣外亮光照人,庭中如昼。渐觉嘈杂声中夹着悲怨啼泣,过后又有顿足捶胸、号恸迫切之声。子邮疑道:“先之声柔怨,后之声愤恨,其中必有事故。”
不免往外看来,把外衣脱卸,腾上垣墙,向前望去,见有一男一妇号呼奔走,另有数人持着火把,劝止挽留。再往远看时,火光人众,约有二三里路远。
子邮跳下垣,赶到跟前,见欲去的男妇俱有六十上下年纪,说道:“清平世界,强将良家女子抢去,我老妇老夫要命做什么!”
劝的人道:“事已如此,只可忍气,恶贯满盈,自有天谴。他此刻有威有势,就系岛主知道,也不甚追究,你们何必枉送性命!”
子邮听得明白,问道:“可是你亲生?那强盗是何人?快些说来,待我追回还你。”
两个老夫妇听得,连忙道:“老汉姓舒名鉴华,抢去的,系老汉亲生女儿。因前日彩桑被幸臣横豪公子看见,托媒议娶为妾,老汉夫妇同女儿俱不肯,那媒人回去,复将聘礼送来丢下,立时走了,今硬使多人将小女抢去。老汉夫妇如何舍得!”
子邮问劝的人:“可是真的么?”
众人指远处火光道:“他女儿现在那里轿中。”
子邮飞步向前,只见护轿约有五六十人哩,子邮故意撞去,皮鞭打来,骂道:“何处瞎眼囚徒,在此讨死!”
子邮左手将轿子捺下,八个轿夫跌倒;右手将鞭子接住,说道:“你们何处强徒,抢夺良家女子!”
将左手朝着那人腰间打去,打倒六人,臂膊已断。子邮丢下,又想前来动手擒拿,走不及的连忙跪下叩头求饶。子邮道:“你们要命,可速将女子送回,若稍迟延,莫要怪我!”
诸人面面相觑,骇慌齐道:“送回,送回,情愿送回!”
只得起身将轿旋转抬回。
子邮在后催赶,脚不停留。正遇见老夫妇两口迎上问信,子邮道:“那不是么?”
鉴华收不住泪,向前扳轿呼道:“薇娥,薇娥!”
轿中应道:“父亲,母亲!”
夫妇大喜叩谢。子邮道:“且待到家不迟。”
夫妇随轿赶去。子邮在后,见俱进舒疃,抬轿人仓惶出来,持火奔窜,料无更变,乃回头寻着车篷,进单家疃。仍跃入垣,上床复寝。
次日起来,盥洗穿衣,见单义领着几个老儿说道:“可是这摸样的?”
老儿细看,摇头道:“不是,不是。”
那人随即出去。
单义复回,子邮问道:“诸人来看什么?”
单义道:“这老儿姓舒名鉴华,无有子嗣,四十余岁生个女儿,名唤薇娥。被那双尾虿看见,欲娶为妾。舒家不愿,双尾虿硬行抢去。忽有异声异服英雄,代为夺转,遁去无迹。闻我家住有足下,要来观看,故叫认认。他说昨所见者,那赳走雄壮的,不似这般温柔书生气象。”
子邮问他:“双尾虿系何等样人?”
单义道:“他父亲是个宠臣,名唤柏彪,又名柏举。他名柏横,家资等于府库,靠着父亲得势。生来力壮身强,养着许多无赖,专在各处唯命是从,无论田园器物,看中的强行占去,谁不畏其凶狠势焰,哪个敢与他较量?”
子邮道:“何不赴都叩阍?”
单义道:“曾有行的,承审大夫瞻徇情面,反吹求疵处,定罪发遣,谁敢再去!所以凶恶愈横,初时称他为恶犬,嗣后更狠,比虿犹甚!所以人皆呼为双尾虿。我看舒家女儿今虽夺转,那双尾虿岂肯轻休?两个老命未必能活也!”
子邮道:“却也堪虞,且看双尾虿可来否?”
单义道:“必来,他是寻事的,今吃大亏,如何不来!明日自有信息。”
却说双尾虿差人役往舒疃,便拭目以待。及到次早,谁知去的轿子抬着个断手门客回来。众人跪下,细细哭诉。双尾虿听得,吼怒如雷,点集二百亲兵,披挂悬鞭,提枪带剑,上骑赶到舒疃,已将中午时分。
单义、子邮闻嘈杂声后,料为薇娥事故,同出竹林望去,果有许多兵马进舒疃去了,乃亦同步前来。只见门前拥挤,都系强壮彪形的军士。闻得里面咆哮渐缓,子邮乃挨身进入。抬头看堂上坐着双尾虿,约三十上下年纪,面如乌炭,发若棕黄,一双突出来的金铃眼,两道竖散去的刷帚眉,鼻孔仰张,嘴唇俯撮,张开五个钉耙指头,指着下面鉴华夫妇并十数老人问道:“那强徒毕竟系何方来的,你们毋得含糊,从实供出,免致全疃涂炭!”
众老人道:“实不知情,求公子爷宽恕,请细访察。”
当有保正向前跪下回道:“这个强徒,便系地方亦俱未见,委属真情。大众谁肯舍身家性命,欺蒙公子?”
双尾虿道:“都如此说,想是过路的,料他也不能逃出旋涡围。今日系吉期,尔们地方人等,代为媒妁,齐备花烛,就在这里成亲,明日带回,即刻办理,不得迟延。”
舒鉴华夫妇在下面涕泣的说不出话来。双尾虿道:“可扶他们入内,好好料理,若仍违拗,连尔等俱莫想活!”
众人向前,将鉴华夫妇拖往后进。子邮随入,只见,哭做一团,诸人亦都下泪。
子邮看不过,乃复出厅来,见阶前礼物酒席堆的盈满,听见报告,俱系左近地方来贺喜的。双尾虿存一席自用,余者俱着分给军士,礼物送往内室。他还带两个家丁,夯着枪鞭,踱将进来,见众人垂泪,房中悲号,大怒道:“可恨这班奴才,违我号令,叫你等立时俱死!军士们可速行缚去砍来!”
家丁接应招呼,外面军士拥入,将众老儿缚起。舒鉴华出来见了,只是跌脚号天。双尾虿道:“你也太无情理,有我这般豪杰女婿,还是哪件不称心?只管啼哭做什么!若非看分上,这样颠倒,要你何用!”乃命去缚。
军士得令,将众者放下。其中有个年事高的,目瞪口张,气出不收,顷刻归阴去了。众流泪抬出。双尾虿哪里管他,大步直向房内行。舒氏连慌关门,双尾虿抬起腿,踢落一扇。
子邮在旁,忍耐不住,乃跨步向前,扳住肩膊,顺势扳回道:“哪里去!”
双尾虿原未提防,竟跌在地,軲辘起来。子邮正欲踩住,背上忽看金风冲下,闪身抓得,却是条银鞭。双尾虿见夺不及,即接过金枪刺来,子邮用鞭挑隔,将枪打得弓弯。双尾虿弃枪跳下堂阶,掣出宝剑,复迎前来。左右兵士齐上,纷纷被鞭击倒。双尾虿见势凶猛,乘空退出。子邮赶到厅上,双尾虿只得回身迎敌,斗过三合,实抵不住,趁众兵赶出时,闪步逃脱上骑,加鞭飞跑。跟的亲军,只道双尾虿仍在内抵敌,无不尽力向前。子邮这条鞭法,似卷狂风,众人哪里遮拦得住,片时间尽行倒地,可怪的是伤的俱系右手。
子邮将壮勇打败,即出来赶双尾虿,看不见踪迹;乃向前晚夺轿的路追过三十余里,到山冈上四顾瞭望,并无形影。寻思道:“今番不能瞒了。”
乃仍向舒疃来。门前围着多人,单义也在内拍掌道:“幸亏英雄,打得好!”
鉴华来拜谢,子邮扶住道:“不必如此。这畜生逃去,岂肯轻休?必定复来,须要防备。可问所伤兵丁根底。”
众人道:“高见不差,亟宜商议。”
舒鉴华道:“伤了兵丁俱逃去矣,请家内坐。”
子邮进见满地血迹,器械纵横。单义视子邮持的银鞭,指说道:“这系双尾虿用的么?好重兵器!”
舒鉴华道:“正是。还有系金枪也不轻。”
抬来看时,与鞭相似。单义取秤平称,各重八斤。鞭长三尺六寸,枪长七尺二寸。子邮道:“这里可有五金匠?”
单义道:“舒家祖代造办军器。”
子邮道:“甚好,可将此枪下炉,弯结盘在鞭端,尖尾伸出,锻如挝样。”
鉴华应允,叫人打扫血迹,白引子邮入左垣炉房。指点半个时辰,收拾如式,却如一条金蛇盘结鞭端。众人看道:“这般老重兵器,莫说使,连担也是费力的。”
子邮道:“可有盔甲么?”
鉴华道:“盔甲虽有,俱属平常,只有单长者家有副貘皮甲,闻系异宝,不肯轻与人看。”
单义道:“诸公只知其一,前之不借看者,非其人也。今遇英雄,而犹悭吝,负此甲矣!但惜无盔,如何是好?”
舒鉴华道:“果然访不出时,只好将就用兼金锻顶暂用。”
子邮道:“只要轻坚。”
鉴华复去指使办盔,单义自去取甲。
当下有个老者道:“双尾虿先说欲洗尽各疃,奈又大亏而去,再来报仇,必定兵多将广,皆不能保。此刻又无诉冤之处,莫如权且齐起壮丁,结约保守,以免立刻涂炭!”
众道:“所见大是,可吹起集众角来。”
于是俱到垣外场上。
不一会儿,只见前后左右,步骑纷纷,各持器械赶奔而至,询问何事。单义甲亦取到。诸老者悉将情由各说与本疃子弟得知,人人愤怒,俱来看子邮,相问见礼。众老者告子邮道:“众丁壮俱愿听受约束。”
子邮看时,约有五六千人,七八百匹马,乃与老者道:“兵可以不用,不可以不备,所持器械,俱系会的么?”
众老答道:“都系会的。我们居处在于边境,常有外岛潜来侵掠,所以器械俱系平常习成的,鲨皮兕革冑甲,俱是人人有的。见了寇船将到,便吹角肃众,以备御敌。所以今日各方闻声俱至。”
子邮道:“如此即易为力,但兵多则费大,而今只留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内、习过器械阵法者,在此教练,其余可各归农。”
遵命分左右站下,入选的有三千人,其余退去。
子邮命各将所习兵器等件,分开各邑,逐样使验,生熟不一。内有二人,一名杨善,一名金汤,武艺较好,令居左右。其余列队,指出不到之处,教其补足;迂赘之处,教其删除,使各习练。又选其尤矫捷者,得蒋钟等七十余人,立健士、裨士、骠士、副士之目,使专项教授。
两天,三千余人俱便捷了。乃令其演阵势,排列作攻击进退之势。其法一人持鲨皮牌,执刀在前;一人或持长矛,或持长戟、长戈在牌后;左右二人持长柄斧,或大砍刀或铲棍棒之类夹护。又一人持短器带弩矢在后,攻则向前发失,战则两边巡护。子邮道:“此合为阵法也。”
众士乃分开,各自为阵,则是迭进者选进,夹攻者夹攻,互相依傍不离。子邮道:“此攻进之法,非受攻受围之法,今须兼之。凡行动,衣食器具须用车载,五人共车一乘,五车为一队。善弓弩长器者,五人登车;善短兵者,五人守车,十人依车而战。每四队为一小阵,用阵长领之;每五小阵为一中阵,用上士率之;四中阵为一大阵,将自统之。今三千人,用二千人分四军,作正兵;一千人为奇兵,内四百人为步兵,作四队,四裨士统率四面救应,六百人为骑兵,作四队,四骠士统率,以为遮前掩后,邀远冲暇之用。行营俱系辎重在中,奇兵在外,正兵在奇兵之外。每夜一健士率所领巡内,一裨士一副士率所领守备,一骠士率所领骑卒,往来远近四方八面巡探。”
余者,交杨善、金汤督率。
却说双尾虿弃众逃回,第三天抵家,父亲出巡不在国中,哭诉与息氏母亲。当下息氏大怒,请外甥白额虎商议,欲邀延猛勇壮士前去报仇。白额虎道:“不可造次。凶徒既能伤表弟及多兵士,则非寻常,必须于五豹将军中,请得两位去,方可收伏。但五豹将军岂能轻动,必须奏闻。”
息氏道:“如何奏闻得?还多系用礼物私请,兼托郎表叔转嘱为妙。况五豹与他父亲俱有交结,谅无不允。”
白额虎道:“所谓奏请,难道叫你将强娶事体言明么?只须如此如此,便可蒙过奏准。”
息氏依汁,次早上朝,启奏道:“前日妄子柏横在边巡视,舒疃众民告诉来有凶徒,扰害地方,强夺良家女子。柏横往前查问,实有其事,是即驱逐,凶徒持强猖獗,反将妾子打伤,殴死从人。若不早为剿火,恐煽动地方,勾引外岛,遗害非小!”
浮金主道:“可着该邑令尉协捕。”
息氏奏道:“此凶徒非令尉所能收擒,妾子柏横在国以勇著名,令尚受伤,令尉何用?必须请发五豹大将,方于事有济。”
浮金主道:“五豹乃镇国将军,岂容轻动?”
息氏奏道:“镇国原为国内事用,令舒疃乃心腹之内,正合用此。”
浮金主问大夫子直道:“卿意若何?”
子直道:“凶徒果狠,自要用猛将擒拿。五豹不可全行,差一二去亦无所碍。”
浮金主准奏,使青豹钱猛、赤豹安大壮两将军前往舒疃,速擒凶犯,审明正法。
二将领命,同息氏出朝,直到柏府。双尾虿迎接,摆酒痛饮。息氏送上许多礼物,再三嘱托,二将满口应允,收礼回家。各便到营内,吩咐众将士来晨齐集听点。
次早入营,拣选精壮将士五百名,预给粮饷半月安家。令即收拾盔甲器械齐全,明早动身,违者以军法论。众军土得令回去。次日清晨,俱在营中伺候。二将同双尾虿全装贯甲,领着人马,放炮起行。
舒疃探事的,连夜奔回报信。子邮道:“任其兵马到此,则地受害。前追双尾虿时,路上有冈,观其形势,颇好守险,莫若移屯彼处,以免过来作践。”
单义道:“此计甚好。前面山冈名聚囊山,又名聚囊谷,原系屯过兵的,今只须到彼处,仍可操练。”
子邮令众士推车移到聚囊山,藏于谷中演习。
第三天探得来军将到,子邮令不必出谷,自携挝单骑下山迎住。双尾虿领三百兵壮先行,撞着子邮,虽有些怕,然恃二豹将军在后,又欺系单身,乃令众兵齐上,自举利斧砍来。子邮见兵士俱系大汉,形状雄壮,想道:“仇不可以结深,只须却敌以求和,不可杀人以积怨。”
乃将骑带转退回。双尾虿只道是惧怕他,举斧骤追。子邮回身迎战。双尾虿到五合上,见有微空,飞斧劈下。子邮往右边闪开,左手早抓住大斧,举起挝来,迎面叫打;双尾虿骇得魂不附体,丢下斧头,往后仰倒,子邮弃斧,也不打下,任奔驰逃去。对面兵壮赶到团团围住,子邮举挝挥使,众人纷纷乱倒,无不受伤。
子邮正欲回山,忽见两骑飞到,后面军将风卷而来。盔甲器械,系青豹、赤豹,也不搭话,举挝迎上。钱猛用筅耙架开,安大壮举枪刺来;子邮钩开耙击下枪,顺势挥回,二人连忙迎隔。斗有十余合,子邮卖个破绽,安大壮挺枪刺胁,子邮将枪杆夹住;见钱猛耙已戳到耳边,用挝架耙,顺柄扫下,钱猛退缩不及,右手正遭,刮得稀烂,弃耙逃回。安大壮因枪退不出来,料想独力无济,亦舍枪而走。子邮道:“赤豹未曾着伤,不可便宜了他!”
乃迫上照肩打下,安大壮急躲时,已落在腿上,将跌下骑来。众军慌来救护,子邮亦不争夺,从容回山。
再说钱猛、安大壮回到营中,俱已痛得要死;双尾虿用丹药灌下,渐渐醒来,喊叫不迭。双尾虿又给敷贴膏丹,扶上帏车,推回京城医治。修书写表,差人飞往都中报信。自领军马守住白骨冈。
钱、安两将到都带伤朝见,逐细奏明。浮金主问道:“此人如何这般凶狠?二卿俱受重伤,实出意料之外。”
道犹未了,只见丹墀内黄豹万胜、白豹冯飞、乌豹真第伏着奏道:“微臣等五人,素称大勇,今忽遭伤其二,臣等不甘,愿同前去雪耻!”
岛主道:“强徒于内地损我猛将,不速擒灭,将为心腹大忧,若入诸岛,国家亦难安枕!今准三卿所请,前去务须小心。寡人另谕威敌侯从西南来,镇邦侯从东北来,会合擒拿,不可纵脱。”
原来威敌侯即是柏彪,乃双尾虿之父,生来膂力过人,系嬖大夫郎福厚之表兄,讨平小岛,官封今职。那镇邦侯姓烛名医,智勇兼全,更长于国家料敌,为浮金第一流人,世袭镇邦侯爵,现为国相。
当下万胜等领命谢恩出朝,传令白、乌二营兵士,同往擒贼,留黄营同赤、青二营余兵居守。三天到白骨冈,双尾虿迎接入营,万胜问道:“连日可曾交战?”
双尾虿道:“不曾。”
玛飞道:“我们来朝会他。”
万胜道:“不可,主上令二侯到来合议后再动。”
真第道:“镇邦文臣,不守也可,威敌到时即可擒贼。”
冯飞道:“逆犯只得一人,我们如许兵将,犹要会齐方能出战,岂不为将来五豹的笑话!我独自擒他!”
双尾虿道:“横与将军同去。”
冯飞大喜。万胜、真第阻挡不住,二将上骑提兵,直往聚囊山。
子邮在冈上,望见双尾虿持斧,领着个穿白提挝的大汉,料系白豹,乃迎下山。双尾虿喊道:“强徒,快来纳命!”
子邮道:“你又钩什么人到此送死?”
冯飞道:“不必胡言!快投首级!”
骤马举挝击到。冯飞的挝,原有八十斤重,若系他人,这挝就躲了。子邮全不放在心上,轻轻拨开,顺便交还。战到十余合,双尾虿见冯飞挝缓,举斧过来。子邮力战二将,斗到酣时,揭去大挝,转照双尾虿面上击下。双尾虿着慌两手横举斧梗迎隔,奈挝力颇重,虎口震裂,斧落地下,转骑便走。冯飞回挝,拦腰击来,想挡住子邮;子邮左手接着大挝,即挥盘蛇挝飞击,正中双尾虿腰胯,打下马来。
这边冯飞双手夺挝,子邮提定,往还两推,冯飞持不住,放手飞跑。子邮追去,冯飞落荒而走。子邮见双层虿爬起欲逃,乃舍冯飞,将缰绳扣于挝干,下马插入地中,赶上双尾虿擒拾起,原挝拦入腰内,上骑解下缰绳时,对过救兵已到。子邮且不接战,两腿将骑连夹,飞跑归营。万胜、冯飞、真第俱追到山上,望见谷中有许多兵士,只道系埋伏的,连慌退下。
万胜报怨冯飞不已,回到塞中,见烛相国已在营内,趋上参见。相国问道:“三位到此,战过几次?”
万胜道:“末将等今早方到,冯飞、柏公子同出接战,柏公子被擒。”
相国问道:“此人系何处来的,此事从何而起?”
万胜道:“末将等奉命擒拿,却不知系何处人,因何事起。”
相国正欲再问,只见巡军入报,西南有彪军马如飞而来。
万胜道:“想系威敌侯至也。”
乃同冯飞、真第出接,果系柏彪,迎上见礼。同进营来,会过烛相国,问万胜道:“小儿何在?”
万胜道:“早晨出战,为强徒所擒。”
柏彪大怒道:“这厮敢如此猖狂,叫我如何耐得下!已有几人被擒。”
万胜道:“无有。”
柏彪愈怒道:“何以单擒我儿?幸喜三位将军无恙!”
冯飞道:“末将几乎丧命。”
柏彪恨道:“这个囚徒,有几条臂膊?”
万胜道:“谷中有伏兵。”
柏彪道:“且下战书,明日阵战,看他如何回答。”
令书使干卒持去。片时,原书上批有八字道:“如命率二三子听教。”
柏彪吩咐准备来朝鏖战。
却说子邮擒双尾虿回营,见追兵俱上山来。蒋钟、金汤禀道:“敌将无知,已入隘内,请令驱杀。”
子邮道:“不可,困兽犹斗,今急蹙之,岂不伤吾手足?谅彼无能久留也。”
远望旌旗纷纷退下。须臾报有敌人投书,骠士风迟呈上。子邮展看,是请斗阵,笑道:“彼亦知我有军矣!”
乃批书付回,命健士杨善、蒋钟、金汤、金璧,骠士雷先、雷声、风静、风迟、明西、周谷,副士卫定、沈杨、山横、石宗、姚安、崔默道:“敌人来朝斗阵,诸子各要小心。杨善、金汤守山,余者各备糇粮,见敌出营,则作风鸦阵势以往。”
众士领命归队。
次日清晨,白骨冈人马出营,蒋钟等饱食,结束停当,随着缓缓下山。子邮指挥,结成金钱阵,其法用十六队居于四隅,四十八队环成圆阵;骑兵张弩带戈矛排于内,步卒持兵杂于骑隙中;用四车高架一车为台,子邮坐于其上。四军令司立四车内,器用各备,左旗右鼓,前形后势。旗主视,鼓主听,形主守,势主击。健士、骠士、裨士、副士,半在队中应敌,半在车前听令。
这边柏彪率三将领、五千雄军,直杀过来,冲突不动。见阵势坚固,令分四面环攻,皆莫能入;又分十二阵相与迭攻。子邮将令旗一麾,左旗司展动黑旗,右鼓司发擂一通,前形司领阵,亦变作十二阵,迭相应敌,虽然抵敌,使无从入,然亦不能杀退敌军。子邮将令旗三麾,左旗司将青旗招展,右鼓司振铎一声,后势司领骑兵齐向四面发弩,此弩名追风弩,能及三百六十步。今两军逼战,相隔不过数步,凡弩一发,穿透数人,如何抵得住?三面俱败退下去,惟西面柏彪自领之军不退,因平日军令最严,恩养备至,又兼军士甲冑俱是鲨皮漆磁的,挽坚牌,持利刃,弩矢莫能深入,所以不退。
子邮将令旗四展,左旗司将白旗扑倒,左鼓司鸣角一声,质势领阵变作舞蝶,西面阵势分开,雷光率骑涌出。柏彪迎上,金璧将鞭指挥,骑俱列于两旁;柏彪舞刀,带领将士冲入。子邮将令旗一卷,有鼓司鸣金一声,阵势复合,柏彪后兵俱为金璧长戈军截断,不能前进。柏彪回头,见有兵随来,只道阵已破了,发狠向前冲杀。子邮将令旗两卷,骠骑围裹将来,风迟、雷声双枪迎上。柏彪全不在意,风静使戟抢入,柏彪力战三将。
沈杨见柏彪犹拚命争持,乃斜入抛起五瓣梅花圈,化作五五二十五朵,向柏彪落将下来。柏彪挥刀挑拨,风静一戟刺入肩窝,雷声、风迟双枪齐中两腿,拍彪大叫,坐不住鞍,跌下骑来。诸将向前缚起,随进来的兵卒尽遭擒获。子邮将柏彪缚于下坐车上。
白骨冈前军马望见,报入营内。相国道:“此欲致我而故激我也。”
传令:“诸将士不得乱动。”
又有报道:“三豹将军俱杀到那边山下去了。”
相国登阜而望,见真第等到聚囊山前,子邮亦单骑出阵。冯飞喊道:“快还我威敌侯来,若有半个不字,叫你立刻分肢断体!”
子邮也不回话,举挝冲进。冯飞使熊掌拍,万胜使龙须鞭,真第使浑钢纵,齐迎向前。盘战良久,子邮顺挝扫开浑钢纵,真第虎口震裂,浑钢纵落下,恰碰伤万胜的马。那马随即倒地,将万胜掀滚下来,腿已受伤。冯飞忙来救护,子邮照肩打到,又跌落马。真第拖着浑钢纵拍马而逃,子邮赶上;真第只得回战,子邮钩住浑钢纵道:“不杀你,任你将两个伤将带回。”
真第道:“真的么?”
子邮道:“大丈夫岂有诳言?”
真第乃下骑,将二人扶起,同坐马上,自己率着军士步回白骨冈。雷光等随退入阵。子邮将令旗三麾,诸军解阵,排队唱凯回谷。
相国看得真切,下视万胜伤微,冯飞臂断,给与灵丹,片时万胜便可按杖行走,冯飞哼声不绝。相国道:“何处降此英才,文武兼全,国内无其匹也!擒而不戳,获而放还,其志岂小!”
想道:“只有这条计策,庶可转祸为福。”
万胜等欣然侧耳。正是:纵子致身遭捆缚,揣情屈已运机谋。
未知是何计策,且听下回分解。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