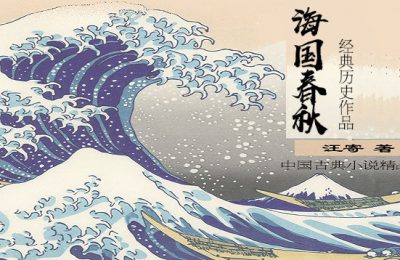海国春秋(原名《希夷梦》)十二卷四十回。作者汪寄,号蜉蝣,新安人。生平不详。乾隆五十一年以前已逝世。据此,盖乾隆时人,书亦著于此时。现存最早的是嘉庆十四年新镌本堂藏板本,又有光绪四年翠筠山房刊本,上海苏报馆校印本,民国年间大达图书供应社排印本。叙述韩速、闾丘仲卿二人在海国建功立业五十年,而两宋兴衰已三百年的故事。清代汪寄著白话长篇神魔小说,《希夷梦》是清代汪寄著白话长篇神魔小说,又名《海国春秋》,四十回,成书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前。此书叙述赵匡胤黄袍加身,举朝归顺。唯韩通全家殉难,李筠起兵讨逆而兵败自杀。韩通弟韩速,李筠幕宾闾丘仲卿,为复仇而投南唐。南唐君臣不思谋国反思媚敌,韩、闾丘离唐往西蜀,途经黄山,被引入希夷老祖洞府。二人安寝石上,乃得一梦,仲卿到海国浮石,韩速到海国浮金,二人各为其主,既立军功又肃吏治。然才过五十年,却遇陆秀夫抱幼主投海,知中原已历三百载,赵氏国亡,元人入主中原。韩、闾丘惊梦,遂从希夷仙去。作品以洋洋50万言讲述一梦幻故事,前所未见,实是作者的一种创造。总之,全书结构、布局比较新颖,故事情节也颇曲折。
《海国春秋》第二回
食周粟不为宋臣 睹覆巢安能完卵
且说仲卿视涧欲投,转念道:“一死虽足以答知己,但大仇谁人能报,周室如何复兴?仍当从长计较。”
止步旋身,不期驴儿正在背后吃草,脚跟恰碰得驴儿的嘴,那驴急掉头时,却撞着仲卿膝腕,单脚站立不住,倒下深崖。足浮手空,满眼漆黑,霎时到底。奇怪肢体全不损伤,亦无痛楚,惟是窈然昏暗。仰望虽有微光,极其高远,摸那石壁与帏幄无二。想道:“若是跌死,倒也罢了,而今不死不活,如何是好?”
再起身用脚试探,似有曲径,虽然窄狭,却能容足。乃盘旋而上,忽见亮光渐大,细看乃是由两个接天的峰头中间漏入,寻思道:“光时上面所见,虽有崇山,如何不见此峰高峻?”
乃更伛偻而上,直至峰麓。往前看去,像两个老少道童,犹立路旁,道士坐在石上。见悬崖边群猿接臂,下饮泉水。再往外望,不期失脚跌落尘埃,乃是从道士袖口滚出。
道士笑道:“足下悟否?何自苦乃尔!”
仲卿道:“小子素爱玄理,并非执迷,奈食人之禄,而不忠人之事,恐亦非仙长所取。素常蒙李节度推解情深,原其所自则皆出于周室。今国虽亡,而潞州信息未知虚实,须回审视。如实无恢复之机,自当披发入山。况有仙长指迷,敢不叩谒法座。”
道士道:“也好,也好!去来,去来!”
老者道:“愿足下切莫去。我游戏未多时,落得几茎白须,请看我哥哥犹是童颜。山外不若山中好,愿足下莫去。”
仲卿看那道童俊秀,不过十四五岁;这老者龙钟,像有八九十岁,如何反称他做哥哥?好生疑惑。道士道:“仲子勿疑。”
指童子道:“这吴槐系汉炎兴庚申所生。”
又指老者道:“这吴贺系汉炎兴甲子所生,同胞兄弟,俱系汉朝国戚吴班之孙。我昔因赴青城山人之请,吴班在青城驾下,极其诚敬。因后主愚顽信佞,料国难守,欲将诸孙托我。因见吴班心地宽厚,选取众中,惟此二人稍有道骨,收为童子。吴槐向来心安笃信,吴贺俗念未除,听见罗公远言唐明皇幸蜀,便要去看。我不阻其出山,幸而根深,犹识归来。看这样子,比他哥哥如何?”
吴贺道:“弟子悔之已晚,所以劝这位客人不必去。”
道士问道:“子意如何?”
仲卿道:“前已言矣,如潞州果失,周不能复,定然回山。”
道士道:“如遇志向与子相类者,可以偕来。”
仲卿道:“领教。”
道士将驴还与仲卿,自己跨上原驴,叱道:“起,起。”
那驴忽然四足云生,腾空而上。吴槐足下亦有云雾,携着吴贺的手,俱冉冉而去。
仲卿恍惚如梦,策蹇驱驰。行不多时,但见崎呕道路尽行平坦,山川顿异,气候亦大悬殊。想道:“方交初热时节,如何便成酷暑?”
深为骇异。忽然大队游兵飞奔前来,为头将官将仲卿细看,喝令拿下。众兵奉命,不由分说,横拖下驴,背绑驱行,押见主将。仲卿低着头,立而不跪,听得上边说道:“吕显,你误了,所获并非仲卿,乃我门生也。”
说话声口,极似相熟,仰首视之,果是曹彬,乃大喊道:“因闻先生扈从屡胜,特来相投,思效微劳。途中突遭掳掠,只道必是潞州兵将,不知却为麾下士卒。”
曹彬下马,向前解缚道:“兵士无知,误犯勿怪。”
命取马来。仲卿道:“原驴甚好,不须赐马。”
军士慌将原驴牵到。曹彬乃同上骑,命吕显道:“我今先行,汝可同闾生到前营来。”
说毕别去。
仲卿薄暮到营,曹彬迎入。仲卿问道:“潞州交兵若何?”
曹彬怅然道:“李公自焚殉国,其子料不能敌,举城投降,今已班师矣。”
仲卿叹道:“吴贺之言不谬,奈何!”
只见牙将禀道:“苗爷拜访。”
曹彬闻光义将到,惊道:“仲卿可急回避,此人到来,恐于君不利。”
仲卿道:“不佞见获,万目所睹,今若逃去,岂不累君?”
曹彬道:“累我事小。”
仲卿道:“检点好名,即见彼亦无恙,何况苗姓?”
言尚未毕,光义已进营门,曹彬出迎入帐。光义道:“故人闾生,闻在将军营内,特来拜访。”
曹彬出将回答,只见仲卿趋出揖道:“苗公别来无恙?开国勋营,古人罕匹,钦敬曷已!”
光义道:“碌碌庸才,因时成事,安得如先生连衡吴、蜀、荆湖,指使淮南、建业,而后齐发并进之奇谋乎!李节度如能始终谨守君言,吾辈皆虏耳。光义此来,非为别事。当今大度,求贤若渴,前日闻先生之策,叹赏再三,行恨不得李牧之意。光义近观星象,见少微隐而复现,移照于兹。今午闻曹公游骑误获闾丘,却系曹将军原来门生大阜。光义与曹将军交最久,向来未闻有吕大阜之名,今隐讳之,定有缘故。是以特来拜访相约,明晨同见圣上。”
仲卿道:“不佞此来,实赴李公之难,以酬知己之情。生且不愿,何知爵禄?蒙公渥爱,来生报答可也!”
光义道:“足下不可执意,大丈夫当以天心为心,顺天之心,以行所学。此尼山之所以与管子也!”
仲卿道:“性各不同,孤竹、柳下,何必相强?君展君才,我守我志,愿毋相逼。”
光义犹欲再劝,曹彬与耳语道:“此公难于急得,且缓几时,或有转移。”
光义点头。忽见军官奔报道:“适到紧急飞报,似乎京内有兵火事件。”
光义因向曹彬道:“四边多垒,人才难得,愿公留意,勿使远扬。”
曹彬道:“敢不从命?”
光义又向仲卿道:“军务倥偬,且暂告别,到汴梁时,再请失陪之愆。”
仲卿道:“愿公努力功名,勿以不佞为意。”
送出揖别。
曹彬使吕显往后营探信,与仲卿携手入帐,道:“光义之意,似不加害。然此处久居无益,弟有黄金二笏,请带为路费。”
仲卿道:“此刻愈不可去矣!适观光义之貌似君子,惜目带鼠形,心地险窄,我去必致累君。莫若明日诡荐不佞,移于彼处,再作区处。”
曹彬称善。
二人对月询谈,小饮多时,吕显回来,曹彬问道:“有何事故?”
吕显禀道:“韩二老爷在汴梁杀指挥使等多人,又放火烧毁数百家房屋,伤了无数将士,已走脱了。”
曹彬惊道:“子邮休矣!”
仲卿道:“子邮何人?”
曹彬道:“韩副都指挥之弟,智勇兼全,何以行此血气之事?周朝难复矣!”
当夜嗟叹不止。
次早起行,光义送函告道:“韩速单身定脱,幸为令弟所擒,收禁府狱,候皇上回朝,究追羽党。”
来人又耳语道:“苗爷特问,昨所劝者,可曾回心?”
曹彬道:“再三婉导,似有转机,但言语反复不定,意欲会到苗公处,朝夕劝谕,庶几有济。”
来人领命而去。曹彬道:“适间所闻如此,子邮已经被擒,现陷缧绁,如何是好?”
仲卿道:“且待弟到汴梁,再作道理。”
少间,只见那人又来,道:“苗公说老爷所见甚好,但不知仲爷可肯过去?苗公就来说话,请暂停片刻。”
曹彬道:“他为我劝得无休,颇有厌烦之意,大约肯去。”
话犹未了,光义已到,各下骑见礼,向仲卿道:“才拙事剧,不揣冒昧,欲请朝夕指示,切愿降临。”
仲卿道:“先生鸿才,夙昔钦仰,如得亲炙,实为万幸。惟有小事奉告在先。”
光义道:“请教。”
仲卿道:“先生勿言一个仕字,不佞宁为先生记室,誓不为赵氏之臣。”
光义道:“昨已闻命,岂敢食言?”
曹彬与仲卿道:“军马业已前行,君之行李另遣送上,不奉陪了。”
又向苗光义耳语道:“慎勿疏忽,至要至要。”
光义称是,相别不提。
下回再说子邮姓韩名速,乃韩都指挥庶母卢氏所出。将产速时,恍惚见伟然丈夫降于庭前道:“我丕豹也,今来托生于汝家。”
随后又有人入来道:“我裴豹也,将来托生于汝家。”
二人争论不已。忽见檐端一位金甲神人厉声道:“吾乃西门豹也,中岳诸葛真君核我有功于民,特命来此托生,汝等何得冒争!”
二人听得,亟自卢氏鼻中入腹,金甲神人亦由口内而入。
卢氏惊醒,立时肚痛不已,只道系个三胞,直至产下,依然只有一个。长成也该豹头环眼,燕颌彪形,却偏形容柔弱,正像女儿。惟有两种异相:每目有三个瞳子,脑后有九个圆骨,如三个品字形状。自幼父母俱丧,韩通延师教之攻书,读过册籍,不喜复看。专好追奔马、接弩箭、刺揉猿、弋鹰鹞为戏,以自娱。韩通乃延名师白参,教习武艺,使带着侄子韩贯在家,攻书习武。不到二年,尽各艺之奥,其膂力与兄相似,而巧捷过之。年方十六岁,正欲将家事付与侄子,自己来京,与国家出力,平定四方。
忽有家人张二奔到,呈上文书,子邮启视变色,与白师傅看道:“太祖、世宗事业,俱成画饼矣,吾兄必死之!臣子殉国,亦理之常。然周朝天下,太祖得之,或未尽善,而世宗以厚泽深仁,天意岂遽绝周!所可虑者,赵党盘结 已久,强豪皆为所笼络,智者陈其谋,勇者效其力。卒然变动,诚不可测。然此刻何能顾得许多,惟有向前,死生非所计也。但此去若得安然,岂患无家?如果变动,命亦不保。”
指着侄子韩贯,向白师傅拜道:“韩氏只此弱息,敢恳先生带回府上,教导成人。”
白师傅躬身扶起道:“忠臣烈士,孝子仁人,皆天地正气,无须多虑。此刻周事已去,贤弟最宜缜密。”
子邮称谢,乃与韩贯道:“为叔的今去赴难,凶多吉少,事势至此,不能顾汝了。我以报国为重,汝以宗祧为重。若周家大事不保,汝他日并须诫训子孙,切不可仕赵。”
韩贯泣拜领命。
子邮想道:“赵氏气势已成,哥哥料不苟生,安能望卵完于巢覆。既是家破人亡,索性将事办理清彻,然后动身。”
乃叫小掌管洪安过来,吩咐道:“将收拾进京两车细软,可另选五匹好壮骡。尔带两个家人,小心服侍白老爷、大相公去。”
又叫掌管高义,传请阖族人齐集。子邮道:“连年来族内未了的事,俱已补全。本府备荒规模,教化法度,矜恤四穷,各款钱粮,俱已经营敷用,无应绸缪者矣。今有国亡家丧之惨,故特请诸尊长降临,敬将田产家资分以各位,每位赠田五十亩,白金百两。仍有余田,将三百亩添入家庙,敢烦于春秋祭祖之后,代速另设席筵,以祭速三代祖先。逢二月、十月,先茔烦代标扫。如蒙不倦存殁,实铭深情。”
众人道:“族中诸件,向来都是令祖、令尊暨贤昆玉维持,谁不沾恩受惠。贤竹林远出,逢时祭扫,应系我们的事,如何还要厚赐?”
子邮道:“诸尊长有所未悉,速此行身命且难自主,何有于家产久远?蒙代祭扫,实为万幸,切勿多辞。”
众人道:“此去定然功成名就,我等权代收管,待荣归之日,还赵就是。”
子邮道:“这也不必。”
送了族众,又叫家内仆婢男妇齐集,每家给银一百两,田五十亩。僮婢各给银五十两。文券悉行焚毁。家人领谢讫,子邮乃命掌管陈俭等四人,收拾行李,叩辞家庙。陈俭、屠泰先行察看,高义、缪机管押行李后走。陈、屠当日动身。
次日,子邮拜别白师傅并族众,跨上紫骝,扬鞭起程。白师傅呼道:“且住!”
子邮勒缰下马。白师傅道:“令侄虽无贤弟磊落,而浑厚潜晦,是其所长,可以放心。贤弟诸事,已造极领,惟忍字功夫未到,须努力于此。”
又拿出宝剑一口,交与子邮道:“此剑名曰无碍,老夫得之四十年,未尝试用。贤弟可紧藏在身边,一者缓急不孤,二者见剑如见老夫。”
子邮拜受,上马加鞭而去。
不说韩贯涕泣及众族人嗟叹分散,仍说子邮晓行夜宿,趱路急切,马不胜劳,到寄春驿另换,驿官见子邮气度,不敢怠慢,问道:“敢请爷示尊姓,所办何差?”
子邮道:“管他作甚!”
驿官道:“原来爷未知,而今新令严紧,恐防奸细冒充,俱设簿籍,登记往来姓名差事。”
子邮道:“有此缘故?在下姓韩,往都指挥府公干。”
驿官道:“爷自何来?”
子邮道:“襄阳。”
驿官道:“樊城即系韩中书爷乡里,爷可系中书爷本家么?”
子邮道:“不是,快备马来。”
驿官道:“现在上料。”
又问道:“爷既说往都指挥府公干,如何又非中书爷本家,难道不知韩爷加赠么?”
子邮惊道:“如何加赠?”
驿官道:“当今皇帝嘉韩爷殉国,是个大忠臣,所以特赠中书令。”
子邮道:“如何殉国?”
驿官道:“此事已久了,爷仍不晓得么?”
子邮道:“我门路远,所以未知。”
驿官道:“正月初旬,当今领兵至陈桥,众将事立为皇帝。韩爷要保周期,众将士围住大杀,韩爷虽刺死多人,亦受重伤,当时殒命。举朝文武,更无阻挡之人。当今登位,不见再有死节者,所以敬重韩爷,加赠中书令。”
子邮大惊,寻思道:“太祖、世宗,何等恩威,今日临难,满朝归叛,难道向日所荣宠者,不是尊崇贤良,竟是代赵家养鹰豢犬?”
又想道:“往时巍巍峨蛾,谈忠说孝,受恩深重者,颇多其人,岂有临危全变之理也?难尽信。此刻倒不必着急,且到前边探访明白,再作区处。”
驿卒牵马来,子邮赏了驿官、驿卒,挎上骤行三十余里,借打中伙,下骑访问,与前相似,数次皆然,乃知是实。直到安南驿上,即于驿旁住下,离汴梁只有九十里。次日,乃易装进汴京城,陈俭、屠泰暗入寓中,诉说实信,相与流涕。见街市比前更加热闹,士卒比前更加严肃。耽搁三日,知是强敌,不胜伤悲,仍出城居住。下午,高义、缪机亦到,子邮道:“汝等如何恁快?”
缪机道:“沿途短雇牲口替换,所以今日得至此地。闻说大老爷已经殉国,又闻并非当今之意,乃军校王、罗等公报私仇,当今闻知,深怪他们擅杀,赠大老爷中书令,如此也还在道理。只是王、罗等这班凶人,却放不过他。”
子邮道:“汝等所见,与我迥殊。王、罗诸贼,成了大爷千古芳名,其恶犹属可耍我等皆周朝臣子,今见巨奸窃夺神器,难共戴天,岂可因他假赠即正?”
陈俭道:“事既如此,且回家乡,另作良图。”
子邮道:“且耽迟数日,可着高义在庙内住,我与你等进城。”
缪机遵命,分开行李,备齐牲口,随着到寓住下。子邮令访旧日家人,俱寻不见。闲住多日,惆怅无聊,忽闻李筠起兵,大喜,欲往相助。当演六壬,得退连茹;复演,又得断娇,嗟叹而止。
不觉春去夏来,宋主遣将往泽、潞后,又行亲征。子邮孤掌难鸣,痛惜失大机会,朝夕惟有嗟吁。
一日,陈俭出南门,看高义回来,忽闻叫道:“陈爷哪里去?”
转头看时,都系当日看后门的邹老儿。陈俭道:“邹伯伯,你在此有何贵干?”
邹老儿道:“亲戚家去。陈爷,你是从哪里来?”
陈俭道:“我是从南来看大老爷的。”
邹老儿道:“大老爷执拗,于正月里全家归天。我因听得风声不好,先就走开,故未遭祸。今我在张琼张爷处看门。”
陈俭道:“好个大老爷,可惜了!”
邹老儿道:“实在可惜,若能不死,也是大富贵。我问你,二爷与少爷好么?”
陈俭道:“都好,二爷现在寓中。”
邹老儿道:“而今想必长成了,可同去看看。”
陈俭领进寓叩见。子邮问是何人,陈俭答道:“是大老爷府内看后门的邹文,今在张琼张爷处管门。”
子邮道:“原来就系见酒埋。”
——这邹老儿最好酒,量又极大,凡见着酒,坐下不动,所以众人起他绰号叫做见酒埋。
当下子邮命陈俭道:“可将好酒烫两壶与他用。”
邹文道:“不敢。”
陈俭取到,子邮问些闲话。邹文吃干,仍不动身。
陈俭又烫一壶,邹文接着自斟。子邮道:“天色已晚,你饮毕可回去,明日无事再来罢。”
邹文道:“无妨,四更回去也不迟。”
子邮道:“那有此理?”
邹文道:“这张爷古怪得紧,日里客来,多回不会。二鼓后有人请见,立刻延入,每每至四五更方散。”
子邮道:“这老儿又系说慌,岂有二鼓后夜夜来往?可知其人姓甚名谁?”
邹文道:“黑暗之中,认不清白,未知姓名。”
子邮道:“岂无称呼?”
邹文道:“一个大爷,一个三爷。大爷认不得,三爷就是常时大老爷在后圃教他参连射法的曹爷。”
子邮问道:“说些什么话?”
邹文道:“不知,大约绝无笑语,常有泣声。”
说说壶又干了,子邮吩咐陈俭如此如此,乃与邹文道:“今使陈俭送你归去,闲时好叫他请你。”
邹文叩谢,同起身回府,买酒复请陈俭。
至二更后,果有人来,道:“三爷请往大爷处。”
陈俭有心,告辞道:“恐主人守待,满领了,明日得闲暇,可往寓内看看。”
邹文拖住,向耳边道:“此刻去不得,须待家爷出门,再随后走。”
陈俭听见脚步响,向窗棂破纸中瞰时,只见张琼低着头先走,有个灯笼在后,同出门去。
陈俭乃别邹文,随着亮影,缓缓而行,忽然人灯俱寂,定睛细看,却系护国寺地方,象贤巷口,想道:“范府正在巷中,二人莫非系会范相?”
乃踅进去,见门掩着,缝内漏出灯光,认得明白回寓,逐细禀复。子邮想道:“范质狐疑,曹彬过慎,张琼性躁,三公虽具忠心,各有病处,所谋难得成就。”
陈俭道:“闻说曹爷奉差,管押军需,往泽州去。”
子邮道:“此中有好机会,惜张、范二公羽翼无多耳!”
陈俭道:“爷何不见张爷商议?”
子邮道:“你明朝仍将邹文叫来。”
陈俭领命,次日去了独回,言“邹文肚腹病重,不能起床”。子邮道:“汝勤视之,待他可以行动,即催前来。”
陈俭答应,日日探视,直到第八日,始同邹文进见。子邮问道:“你如何得病?”
邹文道:“上日曹爷奉差,午后来别张爷,絮絮叨叨,说的不休。忽然军营有旨,召曹爷星夜驰往泽州,办理紧要事件。曹爷匆匆而去。其日使用的人都不在跟前,小的又无计脱身,喉痒难当,寻得剩酒,未曾审视,连壶吸吞,觉得有物在喉,连忙看时,却系大小苍蝇入肚,莫知数目。因此心疑,骤然发作,泻得不休,病倒在床,前日方止。”
子邮道:“今好了么?”
邹文道:“只系两腿无力。”
子邮道:“过几时自然复原,此后逢饮,须要详细。”
邹文道:“是。”
子邮令缪机取酒,陈俭捧出大盘两注,摆在廊下矮桌上。
邹文谢过,笑着右手持注,左手持杯,连斟连饮,二注俱干。子邮命添,陈俭取酒。子邮道:“张爷好么?”
邹文道:“好,昨日奉差公干,今早动身了。”
陈俭酒到,邹文又饮。子邮道:“你的舅子臧公公可惜死了,他家还有何人?”
邹文道:“只有他的堂侄子,系小的的亲内侄,名唤臧联,虽在晦光宫奉侍周太后,却万不及他的表弟倪淹,由圣上宫中出来,何等脸面,王相公、赵相公、陶学士、石节度等诸位老爷求询信息,那个不奉承他?”
子邮道:“各有各道理。我甚思念臧公公,你明日见着内侄,他如得闲,请来这里叙谈叙谈。”
邹文道:“此事容易。我正忘却,曹爷动身时,叫小的托臧联代将奉旨驰往军前的事,转奏太后。张爷今朝亦这般吩咐。此刻亦不可缓了,小的满领老爷的赏。”
子邮道:“如此,我同你去,顺便走走可得么?”
邹文道:“可得,须先问过,方好同去。”
子邮道:“如此,你去顺便问声。”
邹文答应去了。
次日傍晚,来请同行。子邮命陈俭守门,带缪机随邹文到晦光宫。门内小太监呼道:“邹老伯伯今日又来,想系有话与臧公公说。”
邹文道:“正是,烦小公公代我通知。”
小太监应声进去。片刻,臧联出来,邹文告道:“这就系韩都指挥的兄弟韩二爷,与你叔爹爹最好,特为来拜。”
子邮向前施礼,臧联连忙回答道:“原来就系二相公,如今这般长成。可惜令兄大人系个真忠臣,周朝再有如令兄的,安得大位属于他姓?”
子邮道:“公公所言极是。敢问太后与圣上俱安好么?”
臧联道:“目下虽然宁居,终属严墙之下,连咱们亦不知将来是何结局?”
子邮道:“天相吉人,无须过虑。”
臧联道:“相公此来,有何赐教?”
子邮道:“速因受周厚恩,欲朝觐太后、幼主,以表寸衷。欲烦公公代为启奏。”
臧联道:“幼主时刻避嫌,故旧诸臣请觐者,一概不准,即范相相见,亦系深更。相公尊义,咱家代奏罢。”
子邮与袖内取出蒜苗金二条,道:“造次,未带土仪,聊为茶敬,如果不准觐见,则烦代奏韩通亲弟韩速,愿圣下万岁!”
臧联道:“厚赐不敢领,但太后从未许诸臣朝见,此时方命幼主现在东阁读书,相公如要朝觐,明晨可以进宫。”
子邮道:“如此,极蒙雅爱,今且告别,明日五鼓趋来。”
臧联拖住手道:“不可,潞州起义,大军往征,昨有旨到,言汴梁应犯兵火之灾,虽经安排,仍须谨慎,所以夜巡比平日更加严紧。只好屈相公在此草榻,又可省明早之行。”
子邮道:“如此打搅,心甚不安。”
小内监摆出晚膳,邹文道:“二爷在此,小的要回去了。”
子邮道:“请。”
臧联送出,转来入席,通宵说些近事。
不觉晨钟已动,曙色将呈。臧联乃先进宫,约有数刻,回道:“适已奏上,幼主恐有赵家耳目,初时不允。咱又奏明,昨日晚来,并无人晓得,幼主方准。”
子邮道:“感铭不浅。”
跟随臧联直至辟贤殿,仰瞻幼帝已在御座,方面大耳,俨如世宗。行至丹墀,朝觐礼毕,想起世宗,不禁放声哭泣。幼帝垂泪,下座扶起道:“卿为何如此?”
韩速道:“臣誓与赵贼不共戴天,惟恨此刻势若单丝。陛下居身虎口,臣若在外声罪,恐赵贼先无礼于陛下。今欲即请圣驾潜出,巡幸外镇,非若内廷不乏忠良豪杰,讨叛义旗建起,四方自然响应,名正言顺,诛篡贼如振落耳!”
幼帝道:“卿此意却可不必,若天命在周,赵氏自必残灭。今同卿出幸,先离太后膝下,或有惊恐,不孝之罪大矣。且赵氏之兴实由天授。昔先帝忌积习兵强,凡诸臣方面大耳者,多以法去之。赵氏终日在侧,返不能觉,岂非天乎!天命既在赵氏,妄动有何所益?”
韩速正欲复奏,忽见内监引着一人痛哭而入。幼帝大惊,命韩速道:“卿且退。”
子邮只得退出,复请臧联探信。正是:欲知伤缘何事,须托深宫出入人。
不知哭者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