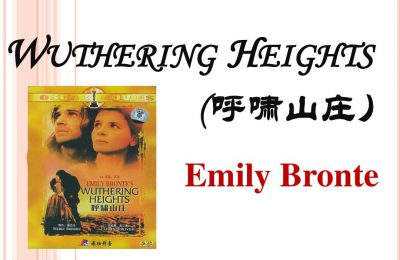《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姐妹之一艾米莉·勃朗特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847年,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被山庄老主人收养后,因受辱和恋爱不遂,外出致富。回来后,对与其女友凯瑟琳结婚的地主林顿及其子女进行报复的故事。全篇充满强烈的反压迫、争幸福的斗争精神,又始终笼罩着离奇、紧张的浪漫气氛。 《呼啸山庄》被公认为世界名著,英国作家毛姆甚至把它奉为世界最杰出的十部小说之一,与《战争与和平》并列。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从1939年已多达十多部。
第九章 · 三
大约到了半夜,我们都还守着没睡,像千军万马般的狂风暴雨降落到山庄上来了。只听得又是风吼,又是雷轰,接着一声巨响,宅子一角的一株大树倒下来了——也不知是给狂风吹折的,还是遭了雷劈;那粗大的树枝压在屋顶上,把东边的烟囱打开了一个大缺口,砖石、煤灰,哗啦啦地落到了厨房间的炉灶里。
我们还道有一个霹雳击落到我们中间来啦!约瑟夫摇摇晃晃地跪倒在地上,祈求上帝不要忘了挪亚族长和罗得族长〔4〕呀,求他就跟当初创世纪时一样,放过了正人君子,只惩罚那班不敬神明的人吧。
〔4〕上帝惩罚罪恶的人间,降下洪水,独有敬神行善的挪亚,因事先得到上帝的启示,躲进方舟,得免于难。约旦河谷地有一罪恶的城市,名所多玛,上帝降天火烧毁该城,唯独敬神的罗得,得上帝指示,逃出城去。
我呢,只觉得这就是降落到我们头上来的末日审判了。在我的心目中,那约拿〔5〕就是欧肖先生。我走去摇动他房门上的把手,看看他这会儿是不是还活着。他在房里回答的那种声气,叫约瑟夫唤天呼地地嚷嚷得更热闹了,好表明像他那样的圣徒,跟像东家那样的罪人之间,横隔着一条不容混淆的界线。
〔5〕约拿,古希伯来族的预言者,因违抗上帝,逃往海中,所乘船只覆没于暴风雨中。
可是二十分钟过后,那一场暴风雨过去了,我们一个个都平安无恙——只除了卡茜。她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因为说什么也没用,她硬是不肯进来躲雨。没戴帽子,也不披肩巾,她只是站在那儿,听凭雨水全都倾泻在她的头发上、衣服上。
她走进来,倒在长靠背椅上,这光景就像从水里捞起来似的;她把头扭过去,对着椅背,双手掩住了脸。
“看你哪,小姐!”我摸着她的肩头嚷道;“你不是存心要给自己找死,是吗?你可知道多晚了?十二点半啦!得啦,睡觉去吧!不用再等那个蠢孩子啦。他是到吉牟屯去了,这会儿他就留在那边了。他想不到我们深更半夜的还在等候他呢——无论如何,他还道只有亨德莱先生一个儿还没睡;他怎么愿意撞在东家手里,叫他来给自己开门呢。”
“不,不;他怎么会在吉牟屯!”约瑟夫嚷道。“他不埋进在泥塘里才怪呢。方才上帝显灵可不跟你开玩笑哪!小姐,我劝你留些儿神吧;下一遭该轮到你啦。一切都要感谢上帝!一切都为了把恩惠赐给从肮脏世界里挑出来、提拔出来的大好人!你们知道《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接着他就引了几段经文,又指点我们去查哪几章、哪几节诗。
我用好话叫这个倔强的姑娘站起来,把湿衣服换去了,可是怎么求她也不中用;我就由着她瑟瑟发抖,由着约瑟夫讲他的经文,只顾抱着小哈里顿去睡了。他睡得那么甜,好像他周围的人个个都睡熟了似的。
我听得约瑟夫继续念了一阵子经文,接着听得他迟缓的步子在爬楼梯,于是我也入睡了。
第二天,我下楼来时,比往常迟了些;借着从百叶窗缝里漏进来的阳光,我看见卡瑟琳小姐还是坐在壁炉边。正屋的门儿也还是半开着,亮光从没有关上的窗子里透进来。亨德莱已经走出房来,踱到了厨房炉边,憔悴无神,还没睡醒的样子。
“你有什么不好过,卡茜?”我走进厨房时,他正在跟她说话;“看你那失神的样子,简直像从水里捞起来的小狗。你怎么脸色这样灰白,身上这样潮湿呀,孩子?”
“我淋湿了!”她勉强回答道,“我冷,就是这么回事。”
“哎哟,她又在淘气了!”我嚷道,看出东家这时候还算清醒。“昨天晚上下着倾盆大雨,她尽在雨里淋着,后来她又在这里坐了一夜,我没法儿劝她动一下。”
欧肖先生吃惊地瞪着眼望我们。“坐了一夜!”他跟着说道。“她不去睡干什么呀?不是怕雷声吧,是吗?几个钟点前就不打雷了。”
只要能隐瞒得过,我们两个谁都不愿提到希克厉出走的事,所以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她打的什么主意,竟坐了一夜;而她听我这么说,也没有什么表示。
早晨的空气清新又凉快,我把格子窗打开了,屋子里立刻涌来了一股花园里的香气。可是卡瑟琳没好声气地叫我道:“爱伦,把窗子关上。我快饿死啦!”她的牙齿在打战,一面蜷缩着身子,向快要熄灭的火炉靠拢些。
“她有病啦,”亨德莱拿起她的手腕说道;“我看这就是她不肯去睡觉的缘故了。他妈的!我不愿意这个宅子里再有人生病来烦我的心了。你干吗要赶到雨里去呀?”
“还不是老脾气,去追那些小伙子!”约瑟夫像老鸦般刺耳地叫道,他趁我们不知该怎么说才好的当儿,抓住机会把他的毒舌头插了进来。
“如果我是你,东家,我就干脆照准他们的脸,把大门碰上了,一个不放进来,管他有身份没身份!你哪一天出去,不是林敦那只公猫就偷偷摸摸地溜了来?还有纳莉小姐——她也是个了不起的丫头哪!——她会坐在厨房里望风,提防你回来;你才打这边儿门进来,他早就打那边儿门溜走了;接下来,咱家那位千金小姐自个儿赶到外边去谈情说爱啦!好正经的行为哪,半夜十二点以后,还钻在田野里,跟那个不学好的下流东西、野种希克厉搞在一起!她们只道我是瞎子,我才没有瞎眼呢——一点儿也不瞎!我看见小林敦进来,看见他出去。
“我还看见你,”(把话锋转向我)“你这个没出息的懒婆娘,你一听到大路上有得得得的马蹄声,知道主人来了,就立刻跳起来,冲到正屋里去。”
“住口,你这个爱偷听的坏人!”卡瑟琳嚷道;“不许你胡说八道,当着我的面!埃德加·林敦是昨天碰巧来的,亨德莱,而且是我叫他走的,因为我知道你一向不愿意跟他见面。”
“卡茜,你在撒谎,还用说,”她的哥哥回答道,“你是一个十足的大傻瓜!可是眼前且不去管林敦;你告诉我——昨天晚上你是不是跟希克厉在一起?要说老实话,现在。你不用怕会对他有什么不利。虽说我还是像平常一样地恨他,没有多久之前他为我做了一件好事,我也就不忍心去折断他的脖子。为了免得闹出这样的事来,我今天早晨就打发他走,叫他自寻生路;等他走了之后,我劝你们都留点儿神吧,我不会有好脸色给你们看的。”
“昨天晚上我根本没看见希克厉,”卡瑟琳回答道,一边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哭得好苦;“要是你当真把他赶出门外,那我就跟着他走。可是只怕你再也办不到了,只怕他早已走啦!”
说到这里,她再也忍不住,竟放声大哭起来,她底下还说些什么话,没人能听懂了。
亨德莱破口大骂,难听的话倾盆大雨般降落到她头上来;他还命令她立即滚回到自个儿房里去,否则,决不会让她白哭这一场的!我逼着她快听话上楼去。啊,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两个进了她的房,她那一场发作的情景——我吓坏了。我只道她是疯了,我求约瑟夫快奔去请大夫。
果然是神经错乱才开始的情况,坎纳斯大夫一瞧见她,就说她病势很凶险。她发高烧。他给她放了血,叫我只给她吃奶浆和薄粥,还得小心防着她跳楼,或是跳窗。然后他就走了——在这教区里尽够他忙的了,从这一家茅屋走到那一家茅屋,两三英里路可不算一回事呢。
虽然我不能说是一个体贴的看护,约瑟夫和东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加上我们那位病人真难伺候。不肯听话,不在哪一个病人之下;但她还是终于渐渐有了起色。
林敦老太太来探望了几次,那是不用说的;并且安排一切,把我们一个个都骂到了,支配到了。在卡瑟琳病后将养的时期,她一定要把她接到画眉田庄去住,我们真是如释重负,心中着实感谢。只是可怜这位老人家,她有理由懊悔她这一番慈爱。她和她的丈夫两个都传染了热病,没有几天工夫,两个老人相继去世了。
我们这位小姐回家来了,比从前更加碰不起,脾气更大,性子更急躁了。希克厉自从雷雨的那一夜以后,从此消息全无。有一天,活该倒霉,她惹得我发急了,我就把他失踪的责任怪在她头上——说实话,不怪她又怪哪一个呢?这一点她自个儿也很明白。
从此以后,接连有几个月,她一直不理睬我,就是跟我说话,也只是主人跟仆人说话的声气。约瑟夫也同样遭受了“逐出教门”〔6〕的处分;尽管这样,他可还是要发牢骚,一本正经地训她,仿佛她还是个小女孩似的。
〔6〕逐出教门,意即断绝往来。基督教会对于被认为犯有严重不敬神行为的教徒的最严厉的处罚,凡是基督教徒都不准和被逐出教门者有任何联系。
她可是把自己看做成年的妇女了,是我们的主妇;而且认为她最近生的那一场大病,给了她一种特权:人家都应该格外的迁就她。偏又是那个大夫关照过,不能太跟她顶牛——一切只能顺着她的心意;而在她的眼里,假使有哪一个胆敢站起来跟她说个不,那无异就在谋害她的性命了。
欧肖先生和他那一帮朋友们,她是避得远远的。她哥哥听了坎纳斯的告诫,十分害怕她脾气一发作就有昏倒的危险,因此逢到她开口有什么要求,总是答应了事;平常也总是十分小心,避免惹起她的火性子。他是反而太纵容她了,对她简直百依百顺。不过这不是出于什么兄妹之爱,而是由于虚荣心。他一心巴望妹子嫁到林敦家去,好给娘家增添光彩。只要她不去腻烦他,那么听凭她把我们像奴隶般作践,他才不管呢!
埃德加·林敦,就像他以前和以后的无数的人们一样,给爱情迷住了。在他父亲过世三年之后,他领着她到吉牟屯的教堂去,那一天,他只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儿了。
我听从了他们的话,却是完全违背自己的意愿,离开呼啸山庄,陪着她来到了这里。小哈里顿差不多快五岁了,我已经开始教他认字母。我们俩的分别是很伤心的,可是卡瑟琳的泪水比我们的哭哭啼啼还要有力量。起先我不肯跟她走,她看见她的央求没法打动我,就到她丈夫和哥哥跟前去哭诉。那做丈夫的答应给我特别优厚的工资;那做哥哥的叫我卷起铺盖上路,说是现在家里已没有女主人,他再用不到女仆人了;至于哈里顿呢,将来牧师自会来照管他的。
这样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听候他们的吩咐。我对东家说,他把正派的人都撵走了,只是为了这个家败起来可以更快些。
我吻了哈里顿,跟他说了再会,从此以后,他和我如同不相干的陌路人了。想到这里真觉得奇怪。可是不用说,他早已把爱伦·丁恩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忘了曾经有一个时候,他是我世上的一切,而我也同样是他世上的一切!
故事讲到这里,那女管家偶然向壁炉架上的时辰钟瞥了一眼,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这时候时针已指在一点半上了。她顿时站了起来,恳求她多留一秒钟也不行。说实话,我自个儿也宁可她把下面的故事留在以后讲下去。
现在她走开去安息了,我沉思了一两个小时,不管我的头脑和四肢又痛又乏,不想动弹,也要鼓起勇气回房去睡了。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