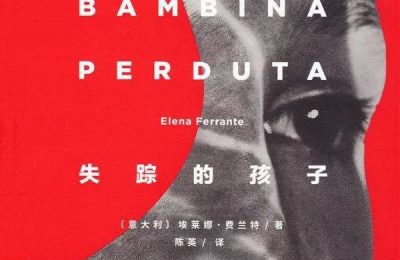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失踪的孩子》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小 说聚焦了莉拉和埃莱娜(“我”)的壮年和晚年,为她们持续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句号。
只有农齐亚和费尔南多为里诺的死感到难过。皮诺奇娅只是做了做样子为丈夫哭了几声,一分钟之后她就好像重生了一样。两个星期之后,她就跑到我家里来,问她能不能取代她婆婆——农齐亚现在沉浸在丧子之痛中,没法再干活,她会在我出去时打扫卫生、做饭,照顾我的女儿,只收取和她婆婆同样的钱。她的手脚没农齐亚那么勤快,但更爱聊天,黛黛、艾尔莎和伊玛相比之下更喜欢她。她说了三个姑娘很多好话,不停地恭维我。她说:“你看起来真漂亮啊,真是个阔太太。我在你衣柜里看到很多漂亮的裙子,还有很多鞋子,能看出来,你是个大人物,和那些重要的人物来往。听说你的小说要改编成电影,是不是真的?”
刚开始,她穿得像一个寡妇,过了一阵子,她就问我有没有不穿的衣服给她,尽管她很胖,穿不上我的衣服。她说:“我会改一改的。”我给她选了几件。她的手很巧,真的把衣服改得很合身。过了几天,她来干活时,穿得就像是去参加聚会一样,她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想让我们说出自己的看法。她对我很感激,有时候她很高兴,不想干活只想聊天,她谈到了伊斯基亚的那段时光。她经常会非常感动地提到布鲁诺·索卡沃,会感叹说:“他死得真惨啊!”有两次她甚至说了一句她非常喜欢的话:“我守了两次寡。”有一天早上她跟我说,里诺作为真正的丈夫只有很少的几年,其他时候他就像小孩子,在床上也一样,一分钟就完事儿,有时候连一分钟都不到。她生气地说,“啊,是的,他一点儿也不成熟,夸夸其谈,爱说谎,还很自负,就像莉娜一样自负,这是他们赛鲁罗家人的特点,他们都是无情而且浮夸的人。”然后她就说起了莉拉的坏话,说她占有了哥哥的劳动成果。我反驳说:“这不是真的,莉娜一直都很爱里诺,是她哥哥一直都在利用她。”皮诺奇娅满脸敌意地看着我,冷不丁地就开始赞美起自己的丈夫。她一字一句地说:“赛鲁罗鞋子是里诺设计的,但莉娜说是她设计的,她利用这一点欺骗了斯特凡诺,让斯特凡诺娶了她,然后从他身上弄了很多钱——我爸爸给我们留了几百万里拉。然后她又和米凯莱·索拉拉联合起来,把我们所有人都毁了。”最后她说:“你不要维护她,你也很清楚。”
当然,这不是真的,事情并非如此。我清楚,皮诺奇娅说这些话是因为以前的恩怨。在她哥哥死后,莉拉唯一的真实反应就是承认了这些谎言。我早就发现,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回忆过去,我惊异地发现自己也是如此,但让我震惊的是,一个人会承认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莉拉马上就说,鞋子的事情都是里诺的功劳。她说,她哥哥从小就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假如不是索拉拉插了一手,那他一定会成为像“菲拉格慕”那样的大品牌。她努力把里诺的生活定格在她父亲的修鞋铺变成了小鞋厂的那个阶段,他做的其他事情,他对莉拉做的事情,都已经一笔勾销了。现在,唯一鲜活的形象就是她哥哥小时候在她暴戾的父亲面前一直在保护她,纵容她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对她来说,这应该是一种缓解痛苦的好办法,因为在同一段时间,她又重新激起了对蒂娜的回忆。她表现得不再像孩子随时都可能回来,而是用一个很阳光的形象来填补家里和她内心的虚空,就好像用一个电脑程序编造出来的一样,蒂娜成了一幅全息图:她在这里,同时也不在这里,莉拉一直都在召唤她。她把女儿拍得好看的照片拿给我看,或者她让我听恩佐给她录的一岁、两岁和三岁的声音,或者会重复她之前提到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她的那些很聪明的回答。提到蒂娜时,她一直用的是现在时:蒂娜有什么,蒂娜做什么,蒂娜说什么。就好像她还在一样。
但这并没让她开朗起来,她比以前更爱大喊大叫了。她对着儿子叫喊,和客户吵架,对着我嚷嚷,和皮诺奇娅嚷嚷,和黛黛、艾尔莎,有时候甚至和伊玛吵架。她尤其会和恩佐嚷嚷,他在工作时会忽然哭起来。但有时候她坐下来,就好像蒂娜刚丢的那阵子一样,她会跟伊玛讲起里诺和蒂娜,就像他们一起出去了。伊玛有时候会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这时候她不会发火,而是说:“他们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但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少了。在我因为几个女儿和莉拉发生冲突之后,她好像再也不需要伊玛了。事实上,慢慢地她很少叫伊玛去她家了,尽管她对伊玛很依恋,但她认为伊玛和两个姐姐一样。有一天晚上,我们刚进到我们那栋楼的楼梯口,艾尔莎抱怨说她看到了一只蟑螂,黛黛一听到蟑螂就恶心,伊玛想让我抱着。这时候莉拉对她们三个说——就好像我不在场一样:“你们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还住在这里干什么,让你们的母亲把你们带走吧。”
-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