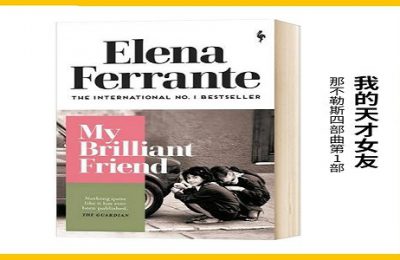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极度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我的天才女友》是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一部,讲述了两个女主人公莉拉和埃莱娜的少女时代。故事一开始,已经功成名就的埃莱娜接到莉拉儿子里诺的电话,说他母亲彻底消失了。埃莱娜想起莉拉对自己命运的预言,于是她写下她们一生的故事……
我发现那不勒斯臭气熏天,非常炎热。对于我的变化——没有青春痘了、晒得黝黑,我母亲没说一句话,只是谴责我提前回去了。
“你做什么了?”她问,“你是不是表现得不好,你老师的亲戚把你赶走了?”
我父亲的态度不一样,他眼睛亮晶晶的,说了很多好话,其中有一句他重复了上百遍,就是:“天呐!我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儿。”我的几个弟弟用很鄙视的语气说:
“真像个黑鬼。”
照镜子时,我自己也觉得很惊异:太阳让我的头发变得金灿灿的,但我的脸、手臂和腿像是被深色的金油刷过一样。在伊斯基亚岛上时,那里的人都晒得黝黑,我淹没在那儿的颜色中,我的变化让自己非常适应那个环境;但现在我回到了这个城区,在这里,每张脸、每条街道都展现出那种病态的惨淡,我觉得自己和环境有些格格不入。人们、居民区,还有车来车往、尘土飞扬的大路,都让我感觉像报纸上印的照片一样黯淡模糊。
我一有机会就跑去找莉拉。我在院子里叫她,她先从窗子探出头来,然后从大门里出来了。她拥抱了我,吻了我的脸,说了很多恭维我的话,都是她之前从来没说过的,那种公然表现出来的亲密让我很不适应。她还是之前的她,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还是有了一些变化,她不再像一个女孩,而更像一个女人——一个至少十八岁的女人,那时候我觉得十八岁已经很大了。那些旧衣服穿在她身上,看起来又短又窄,就好像她在很短的时间内长大了,身体在衣服里呼之欲出。她比之前更高了,肩膀很端正,亭亭玉立,她的脸色很苍白,脖子很细,看起来很娇嫩,她的那种秀美是很罕见的。
我感到她很不安,在路上走着的时候,有好几次她的眼睛看着四周和身后,但她没给我解释原因。她只是说:“你跟我来。”她让我陪她去斯特凡诺家的肉食店。她挽着我的胳膊,我们到了店里。她说:“这件事情我只能和你一起做,幸亏你回来了,我以为我要等到九月底呢。”
我们从来都没有那么亲密地挽着手走路,我们气喘吁吁地向小公园走去,非常幸福地相聚在一起。她跟我说,事情一天比一天糟糕。前一天晚上,马尔切洛带着点心和香槟到了家里,还送给她一颗镶钻戒指。为了避免当着父母的面发生冲突,她当时接受了,把戒指戴在了手指上,但在他离开之前,她毫不客气地在门口把戒指还给了他。马尔切洛抗议了一下,再次威胁了她,却忽然失声痛哭起来。费尔南多和农齐亚马上发现出了状况。她母亲对马尔切洛有好感:她喜欢马尔切洛每天晚上带来的好吃的,也很自豪家里拥有一台电视机;费尔南多觉得自己的苦日子到头了,如果和索拉拉家攀上亲,他的未来就有保障了。就这样,马尔切洛刚走,莉拉的父母就开始审讯她,问她发生了什么,比往常逼迫得更紧。最后的结果是:经过那么长时间后,里诺第一次袒护了她。他叫喊着说,假如妹妹不愿意嫁给马尔切洛那个混蛋,那她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他。如果他们再逼下去的话,他会把一切都烧掉,房子、铺子,还有自己和全家。父子俩又打起来了,农齐亚在中间劝架,邻居都被吵醒了。不仅如此,里诺临睡前非常激动,他忽然就睡过去了,但过了一个小时,他又开始梦游。他们在厨房发现了他,他正在一根接一根地点燃火柴,放在燃气灶上,就好像看是不是漏气。
农齐亚惊恐万分,叫起了莉拉。她对莉拉说:“里诺真的想把我们都烧死。”莉拉跑去看了,她让母亲放心,说:“里诺还在做梦,和他醒着时不一样,他只是担心有没有漏气。”她把哥哥带到了床上,让他接着睡。
“我实在受不了了,”她最后说,“你不知道,我正在经历什么,我必须打破这个局面。”
她紧紧地拥抱了我,就好像我能给她能量。
“你现在很好,”她说,“你一切都很顺,你应该帮我。”
我回答说,她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说,我会全力以赴帮助她。她好像松了一口气,拉着我的胳膊,低声说:
“你看。”
我远远看到太阳底下一个红色的、亮闪闪东西。
“那是什么?”
“你看不见吗。”
“我看不清楚。”
“那是斯特凡诺买的新汽车。”
那辆汽车停在肉食店门口,肉食店扩张了,现在有两个入口,里面挤满了人。那些顾客在排队等候的间隙,会用很羡慕的目光看着那辆车,那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我们的小区从来都没出现过这种车:敞篷车,用玻璃和金属做成,那是阔人才有的车,索拉拉兄弟的“菲亚特1100”简直没法比。
我走近那辆汽车看,这时候莉拉在阴凉处,很警惕地看着街道,就好像时刻防备着自己被强奸。在门槛那里,斯特凡诺探出头来,身上的衬衣油乎乎的,他头很大,额头很高,让人感觉有些比例失调,但并不难看。他穿过马路,很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说:
“你看起来真棒,像个电影明星。”
他看起来也很棒,像我一样,他也被晒黑了,也许整个城区,只有我们俩看起来很健康。我对他说:
“你晒得真黑啊。”
“我放了一个星期的假。”
“你去哪里了?”
“伊斯基亚岛。”
“我也在伊斯基亚。”
“我知道。莉拉跟我说了:我在伊斯基亚找了你,但一直没找到。”
我用手指着汽车。
“真漂亮。”
斯特凡诺的脸上泛起了一丝很有节制的得意,他指着莉拉,用充满兴趣的目光打量着她,对我说:
“这是我给你朋友买的,但她一直不相信。”
我看着莉拉,她在阴凉处,非常严肃,表情有些僵。斯特凡诺用有些讽刺的语气对她说:“现在莱农奇娅回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莉拉用一种几乎有些遭罪的语气说:“我们走吧!但你要记住,你邀请的是她,而不是我,我只是给你们做伴的。”
他笑了一下,回到商店里。
“发生了什么事?”我有些迷茫地问。
“我不知道。”她回答说。她想说她不知道自己具体在搞什么。她看起来像在算一道很难的数学题,但表情并不像往常那样放肆,她看起来显然很担心,就好像正在做一个实验,但对结果并不是很确信。“一切都开始于斯特凡诺买了这辆汽车。”她对我说,他开始就像开玩笑,但后来越来越严肃,他说买这辆车子是为了她,是为了能打开车门请她坐上去,至少一次。“这车只适合你坐。”他是这么对莉拉说的。从七月底他们把车子交付给他开始,他就一直请求她上去,但他的方式很客气,并不烦人。他请求她先和阿方索坐上他开的车兜一圈,然后是和皮诺奇娅,最后和他母亲,但她一直都回绝了。最后她终于答应他了,她说:“等莱农奇娅从伊斯基亚回来时,我再和你兜风。”现在,我们在那里,该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
“他知道马尔切洛的事情吗?”
“他当然知道。”
“然后呢?”
“他还是坚持要那么做。”
“我很害怕,莉拉。”
“你记不记得,我们做了多少让人害怕的事情?我特意等你回来。”
斯特凡诺回来时脱掉了白褂子,他头发很黑,脸色也很黝黑,眼睛又黑又亮,他穿着白衬衣、黑裤子。他打开汽车门,坐到方向盘后,打开了车篷。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我坐到后排的位子上,但莉拉拦住了我,她自己坐在了后面。我很不自在地坐在了斯特凡诺旁边。他马上开动车子,向新修建的小区方向开去。
风很凉爽,我觉得很舒服,我陶醉于汽车的速度,同时也陶醉于斯特凡诺·卡拉奇的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和平静。我觉得,虽然莉拉没说什么,但她已经向我解释了一切。事情就是这样:那辆鲜红色的跑车买来就是为了载着她兜风的,这只是开始。事实上,尽管那个开车的年轻人知道马尔切洛·索拉拉的事,他正在打破男人间的规矩,但并没有明显的不安。是的,我当时在车上,忽然被卷进了那件事,我的出现可以掩盖他们之间的一些私密谈话,甚至他们的关系。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当然,这一圈兜下来,会发生一些比较重要的事。莉拉自己不知道,也不想告诉我那些具体的事情让我理解。她是怎么想的呢?她不可能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要比她从墨水瓶里向外甩纸片更糟糕。然而,极有可能,她也不知道自己具体要干什么。她就是这样,会打破平衡,就是为了看到有没有另一种方式可以重新恢复平衡。因此,我们坐在跑车上,头发在风中散开,斯特凡诺驾驶技术非常熟练,他心满意足,我坐在他旁边,就像是他的女朋友。我想着他说我像一个电影明星时的目光,想着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喜欢我超过喜欢我的朋友。我想着马尔切洛·索拉拉可能会向他开枪,就觉得不寒而栗。他潇洒自信的动作,会像莉拉描述铜锅一样,不再那么牢不可破。
我们朝那些新建的楼房开去,就是为了避免经过索拉拉酒吧前面。
“我不在乎马尔切洛是不是能看到我们,”斯特凡诺平静地说,“但如果你在乎的话,那我们绕过去。”
我们钻进了隧道,向海边方向开去。很多年之前我和莉拉一起走过那条路,就是后来下雨的那次。我提到了那次经历,她笑了,斯特凡诺想让我们讲讲。我们讲了那次出行的所有经过,大家很开心,最后我们到了格拉尼里。
“你们觉得怎么样?速度挺快的,是不是?”
“非常快。”我热情地说。
莉拉没有做任何评论。她看着四周,时不时会拍着我的肩膀,给我指那些房子,还有路上衣衫褴褛的人,就好像她得到了一个结论,一件我应该马上明白的事情。最后,没有任何前言,她很严肃地问斯特凡诺:
“你真的和别人不一样吗?”
他在后视镜里寻找她的眼睛。
“和谁不一样?”
“你知道的。”
他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他用方言说:
“你想让我说实话吗?”
“是的。”
“我的出发点是那样的,但我不知道事情会有什么结果。”
我那时候才发现,莉拉一定是有很多事没告诉我。那种充满暗示的语气证明了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他们已经在其他时候交谈过了,不是开玩笑,而是很严肃地谈过了。我在伊斯基亚的那段时间到底错过了什么?我转过身去看她,她没有回答。我想是斯特凡诺的回答太模糊了,让她有些烦躁。我看到她在阳光下眯着眼睛,衬衣鼓鼓的,胸口在起伏,风灌进了她的衣服。
“这地方要比我们那里还穷,”说完这些,她又笑着说,“你不要以为我忘了你想扎我舌头的事。”
斯特凡诺点了点头。
“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了。”他说。
“你那时候个子是我的两倍高,真是欺软怕硬。”
他有些尴尬地微笑了一下,没接她的话茬,加速向港口方向开去。这次兜风不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向雷蒂费洛区和加里波第广场方向开去。
“你哥哥状态不好。”我们快到小区跟前时,斯特凡诺说。他还是从后视镜里看她,然后问:“橱窗里展示的那双鞋子,就是你们做的吗?”
“做鞋的事情,你又不懂!”
“里诺一直在说那双鞋。”
“还有呢?”
“那双鞋很漂亮。”
她眯起了眼睛,好像眼睛快要闭上一样。
“那你就买了吧。”她用通常那种挑衅的语气说。
“你们要卖多少钱?”
“你要和我父亲谈。”
斯特凡诺很果断地掉头了,我一下子撞在车门上,我们向修鞋的铺子方向开去。
“你要做什么?”莉拉问,她满脸惊恐。
“你说让我买了,我现在就去买。”
-1.gif)